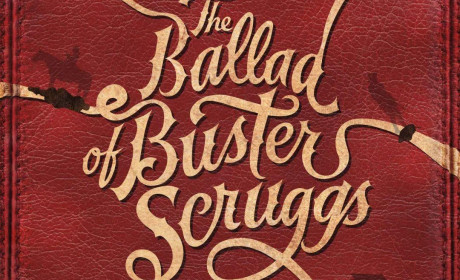流放与自赎:宿命萦绕下的西部叙事
我知道在边界的对面还有一个牧场,那里有青山、绿草和溪流,另外还有间修葺了一半的小木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可以在那儿安身落户,你愿意去吗? —— 《关山飞渡》
内布拉斯加以西
在研究早期波兰学派电影的产生和流变时,有学者指出:“具有民族化特征的地理风景往往在视听语言的运用过程中被赋予某种象征性含义,这使得其往往成为个人自我价值认同与民族主体意识之间生成联系的纽带。”

自十八世纪末期展开西进运动以来,美国版图得到大规模扩张的同时,社会政治,经济和阶级格局也发生深刻转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坚实、乐观、无所畏惧的标签化民族精神得以被塑造而成。西部电影随之诞生,作为一种独立的类型化叙事产物,其所构建无可替代的人物心理状态成为时代的缩影。
从《关山飞渡》到《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西部片经历了从诞生到鼎盛,从衰落到复苏的历变,同时也是电影摆脱“泛标签化”,逐步走向个人风格成熟,主体层次鲜明的“去好莱坞”的过程。
回归
由科恩兄弟执导的影片《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在第七十五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斩获最佳剧本奖,这也是科恩兄弟首次使用数字摄影机拍摄的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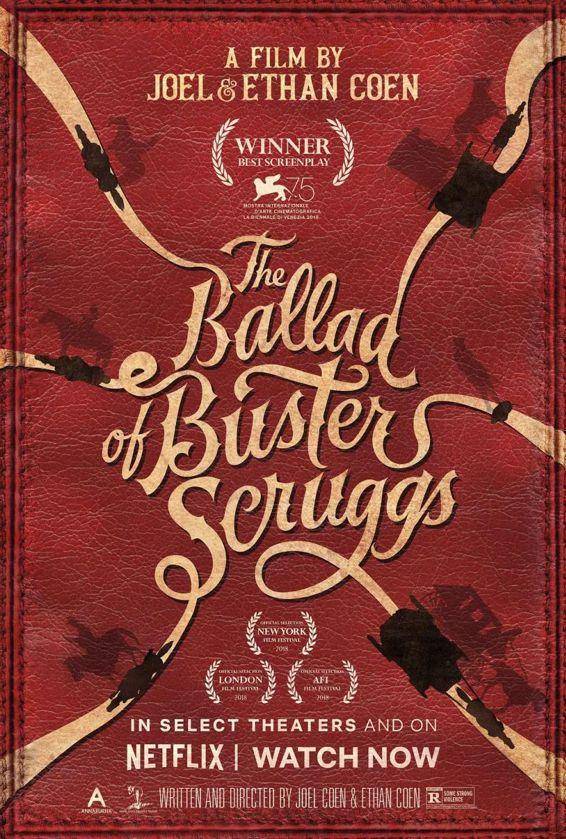
影片按章节的形式划分,以共同的情感基调和深层内涵讲述了六个不同的西部故事:
绰号为“圣萨巴妙音鸟”的巴斯特斯克鲁格斯历经数次战无不胜的决斗之后最终倒在对手的枪口之下;
年轻的牛仔抢劫银行未果被逮捕,阴差阳错逃出生天之后再次落入法网,最终失去生命;
四肢皆无的艺术家因难以取悦观众而被剧团经理投入湍急的河水之中;
年事已高的淘金者偶然发现金矿,却在功之将成时受人偷袭,终于他反败为胜,满载而归;
艾莉丝在迁徙的路上同镖客纳普相爱,正当两人准备结婚时艾莉丝却因意外丧命;
五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同乘一辆马车,旅途上他们各自分享自己的独特经历,来路各异,殊途同归。
宿命
影片出自于原创剧本,导演首先以叙述者的身份交代影片中所有的故事都来自于同名小说,继而将其文字以声画的形式呈现在银幕之上。这使得影片首先构建起一个沉浸和抽离相交互的语境。

主人公时不时面对摄影机直接同观众展开独白,保持着人物同观众之间的认同距离,加深陌生化效果,强调的并非人物主体而是人物整个生命历程在影像中的浓缩。
影片充斥着浓厚的“宿命感”。宿命从本质来说是命运,然而相对于虚无缥缈的命运本身,宿命往往为某种力量所支撑,它雁过留声,有迹可循,人物往往身陷其中,难以脱身。

无论是斯克鲁格斯倒下时意识到百密终有一疏的道理,还是在牛仔受刑时最后一眼看到美丽的姑娘,他们的死亡都被赋予一种戏谑,调侃的意味。
死之于其成为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死亡成为其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对于人物而言,人生不存在节点,死亡本身便是节点。

他们脑海中是否重现一生的图景,又是否接受到上帝的救赎这不得而知,唯一明晰的是他们生于当下,死于当下,西部本就是如此。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个故事《受惊女子》中,作为女性的艾莉丝挣扎于时代的洪流中,她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被迫接受来自陌生人婚约。而当她同纳普相爱之后,却又无法逃脱命运调侃似的捉弄。

作者准确地把握住宿命的每一个能动瞬间,在这样的瞬间里,人物被迫做出选择,而备选的往往只有一个答案,这是支撑整个西部世界共同的内在动力。
漫天繁星是流动的长河
自西部片出现以来,在由单一叙事结构到多层次线索铺排转变,由展现个体自我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共同指涉到深入主体内心以探求其难以寻觅命运踪迹的过程中,镜头也记录并还原了极具浪漫色彩的西部世界本身。

从纪念碑谷广袤远阔的红色磐石到特顿山脉一望无际的雪霜苔原,影像里的龙血树从湖水倒映着的晚照间穿过,飞驰的马从山间倾泻而下,长驱直入深谷如入云端。
月下树影吞没细碎的沙粒,满目黄沙孤静地吟唱颂歌,裹挟着一切共同成为难以忘怀的回忆。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说:“让一个人置身于变幻无穷的环境中,让他与数不尽或远或近的人物错身而过,让他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这就是电影的意义。”
生命是黑夜前的漫长旅程,是电光火石,是戛然而止的交响,是水面上你来我往。
以生命的形式存在于世界的维度里,我们握手言和,我们言谈甚欢,我们共享彼此看法,最终互相拥抱,一起跃入宿命的深渊。
这或许就是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

 影形人
影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