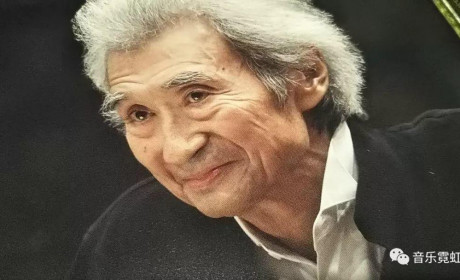《指挥家》底层移民女孩 攻克着重重阻碍成为指挥家
荷兰电影《指挥家》是近期引进片里质量不错的一部。
励志、热血、年代戏质感十足。
但是如果深究起来,主打“女性主义”的本片仍然有着这一系影片的常见弊端。
指挥家:披着女权外衣的闯关玛丽苏文|康怡作者简介:职业记者、兼职主持、专业翻译、业余声优。

01
《指挥家》是一部出现在正确时代的正确电影。
简单来说,它讲的是世界第一位女指挥家安东尼娅·布里克在男人占绝对领导地位的古典音乐届的奋斗史。
布里克是一个出身寒微的私生女,她跟随贫穷的养父母漂洋过海从荷兰移民美国。在女性地位普遍低下的1920年代,社会对她的期待是找个男人嫁了,再生下一串孩子。可她的选择不仅是追求一份独立的事业,而且还是成为对当时女性而言难于登天的交响乐指挥。
从对男性言听计从,到指挥一整个乐团的男人,这种对立为故事提供了足够的戏剧性。

《指挥家》是历史上第一名女性指挥家安东尼娅·布里克的传记,她出身贫寒,后来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古典音乐领域取得一席之地。
在长达138分钟的篇幅里,女主角几乎无暇喘息,全程开足马力攻克着一个又一个阻碍其成为指挥家的困难,从拜师、入学,到恋爱、寻亲、欧洲成名,再回到美国奋斗,密集的事件撑起了影片的全部,观众很容易迅速代入打怪升级的节奏,并在主角一次次与各种厌女症的男性角色交锋时感到同仇敌忾的爽快。
这个底层移民女孩,身上贴满了“边缘”的标签,它们把她作为一个人的可能性无限缩小。而她热爱的音乐艺术,则是人间一桩不问出处贵贱的美好。虽然是有真实人物原型的影片,所谓“结局”也不甚意外,我们依然会跟着主人公每一次小小的胜利而激动、会心。那种饱含天真一根筋的热血,就是令人向往的成人童话。

女主角在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的路上处处碰壁。
02
可惜的是,在高密度的励志事件之余,《指挥家》没能呈现出完整立体的人物画像。
本片编剧兼导演、荷兰女导演玛利亚·彼得斯意不在拍摄一部忠实而严肃的传记片。她集齐了女权、性骚扰、跨性别等时下最具话题性的元素,杂糅而出的,其实是一部“爽片”。她似乎并不真正关心主人公作为一个人,以及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心风景,我们只看到目标和事件,却很难捕捉到主人公在朝着梦想靠近的过程中心智与情感的发展变化,或是她在艺术上追求的升华。
甚而连贯穿影片的爱情线,也走的是玛丽苏路线。抱有音乐梦想的贫寒女孩,遇上出身世家、从事音乐经纪的多金帅哥,二人从欢喜冤家发展成恋人,却因女主追求指挥事业分开,但在女主回到纽约发展山穷水尽的时候,帅哥又默默地四处联络,最后请出第一夫人站台,从而成就女主执棒的纽约女子交响乐团。

电影没有跳脱出女主角需要白马王子的俗套剧情。
帅哥之于女主,就像大部分邦德女郎之于007,是一个“好看”的点缀,他只负责无条件的痴情。二人的恋情发生得迅速而突兀,而当女主选择远赴欧洲拜师的时候,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对男友的留恋。只有在孤独受挫时,才想到给对方写信,并在得知对方订婚的消息后突然狂躁暴走。
我们甚至会怀疑,女主到底有没有爱过这个肌肉发达得要撑破衬衫的痴情男。恐怕多半是没有,因为影片对于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角色的描写,也是扁平而乏善可陈。他更像是个憨憨的工具人,来填充女主爱情的履历,并在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
一部围绕人物展开的电影抛弃了对人物的探索,很容易令人感到不知所云且审美疲劳,更无法对她每一个行为的动机抱有理解和关切。

男主角成了“工具人”,这恰是许多电影中女性所起的作用。
影片以近乎八股文式的齐整对仗,对女性处境进行了符号化的叙述,如影片首尾女主成功前后与男性在台上台下位置的对调,钢琴教师对其骚扰不成反咬一口并断言“女人的位置就该在下面”的讽刺等等。
而女主的形象,也因为缺乏细致的描摹,仅仅呈现出暴躁而捉摸不定的一面,仿佛只有打破传统的温柔,靠近男性身上的霸道和独裁,才能让她登上指挥台变得顺理成章。
03
在Me too运动的背景下,这部电影和许多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一样,撞到了正确而讨巧的题材,也得到了不错的风评。
但说到底,当我们在电影中谈论女权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呢?其实,近观相当一部分影片,就会发现政治正确本质上只是另一种包装优雅的政治,那当中也暗藏着许多陷阱。从社会文化强加给一个性别的刻板印象中挣脱出来的方法,不该是向另一性别的刻板印象的转换。这样非此即彼的轮转,终究是以暴制暴且伤人伤己。
私以为,电影所能提供的“最女权”的东西,就是真实地描绘女性。无论是她们的痛苦、软弱、卑微,还是智慧、才华、勇敢,都毫不回避地去探索,不羞于展示人性最私密而暧昧的形态。

“女权”意味着敢于呈现女性最真实,最有人性化的一面。
近年有两部令我印象深刻的女性电影,都由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分别是《她》和《将来的事》。两部影片虽然风格大相径庭,但都贡献了极具特色的丰满女性形象。前者是遭到性侵的女企业家复仇记,后者则以淡雅的文艺片格调,讲述了哲学女教师中年失婚后的挣扎以及对自我进行的智性的救赎。
这两部影片里的女主都拥有独立完整的人格,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弱点,都经历过变故,围绕她们的男性有的可爱有的可恨有的可怜——正像她们自己一样。而她们带着创伤努力活下去的姿态,才分外动人。
据说由于角色的争议性,《她》在选角时被众多好莱坞女演员拒绝,最终定下了63岁的于佩尔。某种程度上,这也体现了美国和欧洲在今天的语境下对女权的不同理解。

于佩尔在《她》(2016)中饰演一位被性侵的女强人,她凭该角色拿到2017年法国恺撒奖和美国金球奖的影后。
又如早在Me too运动之初,法国国宝级女演员凯瑟琳·德纳芙就曾在《世界报》上反对美国的一刀切做法,她认为好莱坞的做法已经令人们噤若寒蝉,伤害了“调情的权利”。而这位已过80高龄的女演员早在几十年前,又曾与300多名各界女性联合上书要求堕胎合法化,被同一份法国报纸称为“343个婊子的宣言”。
这里无意讨论女权运动的方向与边界,只是回归到作品上来说,电影有别于政治,它应该首先承认女人是人,在这个前提下去呈现女性生而为人的复杂性和可能性,而不是去展示“女人该有的样子”。

凯瑟琳·德纳芙在《白日美人》中饰演一位幻想当妓女、出轨的中产家庭的太太。
同样地,性别平等也不是女儿国式的反转乌托邦,每一个精彩的女性故事里,如果男性缺席,也难以成立。讨论男性在刻板印象下的不自由,对女性有重要的意义。
《指挥家》在女主成功举行了女子交响乐团演出的胜利中高亢结尾。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一段文字,大意是人物原型安东尼娅·布里克的纽约女子交响乐团只坚持了数年就被迫解散,她本人虽一生致力于女性在古典乐届的发展,但从未成功受聘成为任何乐团的常驻指挥家。
这段令人泄气的事实补充,与影片的一路高燃恰恰无意中揭示了这个女权作为政治符号被滥用的时代的真相,其讽刺性远深于那138分钟的偶像剧。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职场、资产、社会地位、家庭承担等各项调查的结果显示,与十年前相比,其实我们离平等反而更远了。女性主义被大量谈及,它成了一种时髦,一场声势浩大的秀,但它并不对应现实,甚而还常被利用,不易察觉地延续并扩大着性别的暴力。


 影形人
影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