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不一样的马拉松 如何面对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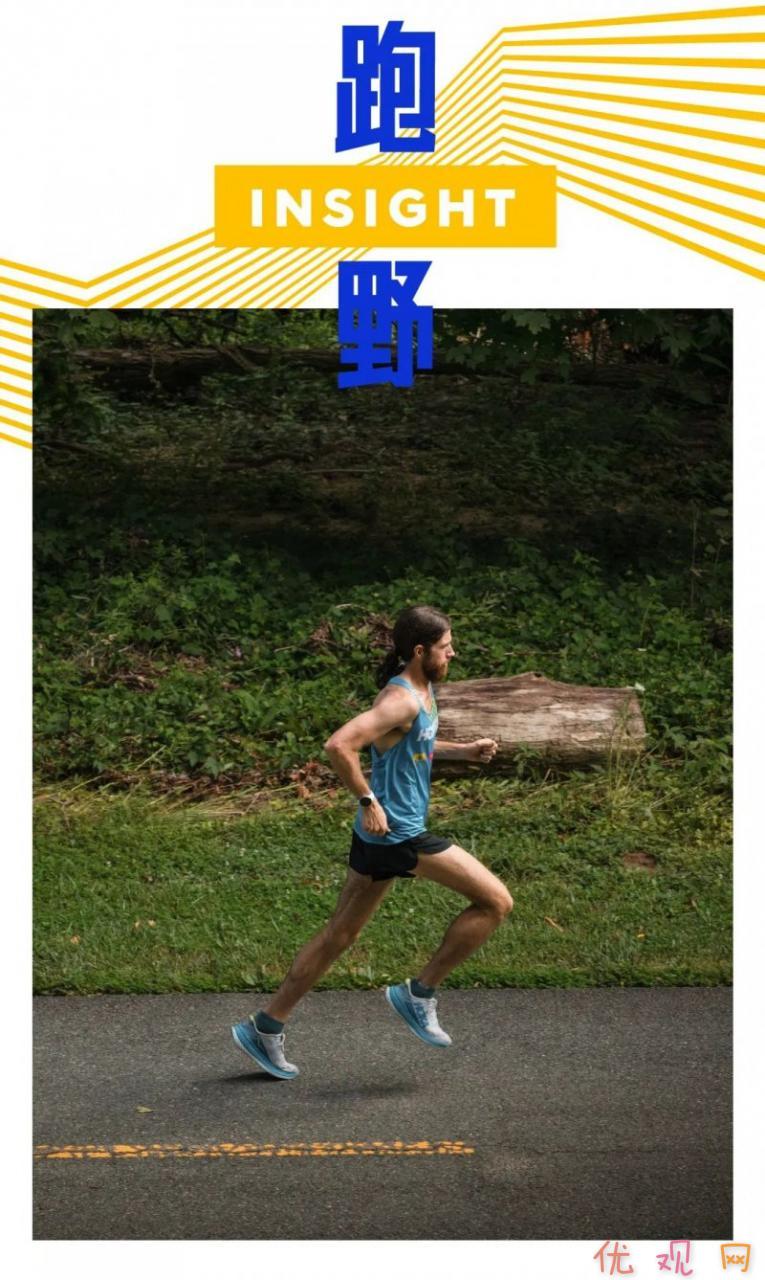
新冠疫情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线的马拉松比赛,我们该如何赢得这场胜利?
在任何耐力比赛中,人们都希望能看到一个终点,在新冠肆虐全球之际,虽然疫苗研究已经取得了突破,也开始安排重点人员进行接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眼下距离人们心目中的终点,仍然一段未知的旅程。对我们来说,幻想一个遥不可及的未来不如活在当下。

你能想象一场跑步比赛需要坚持43个小时以上吗?当全球都饱受新冠困扰时,闲不住的跑者们又跑出了新花样——隔离版超级后院线上超马(Quarantine Backyard Ultra)。参赛者每个小时内都要完成6.7公里,直到放弃为止,这场比赛没有终点线,会一直比到只剩最后一人。这场比赛对跑者的考验就像当下的新冠疫情,煎熬又看不到尽头。

当比赛进行到43个小时之际,比赛只剩下最后的三位选手,Michael Wardian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来自弗吉尼亚的45岁跑者回忆起自己在完成第43小时的比赛时,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我不想再继续了!”

我们与COVID-19的斗争不是一场短跑比赛,而是一场持久的马拉松,甚至当美国人民把特朗普都熬下台后,这场斗争依然还是充满着问号。马拉松,甚至是超马,通常都会有明确的终点线。对于参加了隔离版超级后院线上超马的2400名跑者而言,这种开放式的赛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挑战,首先是策略上的挑战(如何在没有终点的情况下调整配速及补给),然后是心态的挑战,最后是存在性的挑战。

终点预期理论,这是一个体育学一直在研究的课题。而这个术语是德国生理学家Hans-Volkhart Ulmer于1996年提出的,用来描述终点(或目的)对整个过程的体验会有怎么样的影响。研究人员研究了当隐藏终点线、秘密移动终点线、或完全撤走终点线时会发生的情况。
10月4日的伦敦马拉松比赛中,由于新冠大流行,以往沿泰晤士河路线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精英跑者们将绕着圣詹姆斯公园的闭环赛道比赛。而12月6日举行的瓦伦西亚马拉松则依然是在开放的赛道进行,而瓦伦西亚的赛道也诞生了去年男子马拉松最好成绩2:03:00。当然,天气、比赛状态等因素也有关联,但终点的设置形式是值得考虑的地方。

如果车的油箱中只有一定量的燃料,而又必须行进一定的距离,那么我们还是可以算出刚刚用完油跑到终点所需的速度。这个看似合理的方式如果用在跑者身上却是行不通的。
在比赛中,人们熟悉的场景是,跑者们绕过最后一个弯道,看到终点线时冲刺通过。这并不是经验不足,即使实际上最优秀的运动员也会这么做。一项针对近一百年的5000米和10000米以上的世界纪录的分析发现,在67%的情况下,最后一公里的配速是整场比赛中最快的,其余的情况,最后一公里的配速是第二快的。任何关于你有多接近精疲力竭的讨论都暗含着一种假设,即你离终点有多近。

这种自我保护机制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其细节仍有所争议,但这种模式已经根深蒂固。在Ulmer教授1996年的论文中,他通过在跑者、自行车运动员和游泳运动员身上的实验说明了他的想法,但他还推测了候鸟的行为,例如,多吃点东西可以使鸟类一口气飞行更长的时间,但同时又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并且让它们由于体重的额外增加而在飞行中燃烧更多的能量。鸟类能够成功权衡所有因素并做出正确的飞行决策以(仅勉强地)准时到达目的地的唯一方法是,它们是否具有某种对于终点的内在或后天所获的知识。

固定的终点会让人预设出完全力竭的感觉。一跑过终点线,我们就筋疲力尽了,但其实力竭的过程是慢慢接近并越过终点线的整个过程。如果没有终点这个目标,我们很难可以弄清我们到底离自己的极限有多远。

在那场看不见终点的比赛中,当Wardian决定退出时,他的对手只剩下了一名在跑步机上跑的捷克男选手和一名在积雪上清出的环道上跑的瑞典女选手。第三天黎明的几小时前,他走到自己在屋外搭的帐篷里,告诉他的妻子,他不想继续了,他的妻子正在帮他做一些参赛的协助工作。她回答道,“这不是个好借口。”他考虑了一下,认为她是对的。于是他又坚持了一轮。

终点线可以让你跑得更快,这主要是因为你会在接近终点的过程中加快速度。很明显:如果可以选择已知和未知,一定要选前者。但更难的是,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该怎么做,就像如今我们所处的这个形势之下。
很自然的一个想法是自己假想出一个终点。例如,在隔离版超级后院线上超马比赛中,比赛开始后23小时的时候,还剩下了77位跑者。当160公里(跑了整整一整天)这个里程碑接近时,那一轮只有一位跑者退出。但是第24小时或25小时后,其中剩下的一半以上的选手们都退出了比赛。专注于假想的终点线可能可以帮助他们度过一段中途黑暗的时光,但一旦越过了这个终点线,他们很快就会绝望了。

我隐约记得3月安大略省宣布第一次学校停课。那是在三月休息后的两个礼拜。作为两个小孩的父亲,那种麻烦而混乱的程度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就像闻到恶臭时暂时憋气一样,我知道我的生活可以暂时停一停,直到熬过这一阵。
当封城(或者说社交隔离)的时间延长时,我知道我还可以坚持。然后又一次,延长再延长,我越来越难说服自己一切都快结束了,我不得不进行调整,找到一种可以坚持下去的方法,而不是把一切都推到“一切都结束“。你只能憋气憋那么久。

随着夏天的时候情况看似开始好转,坚持下去变得很有可能,我几乎说服了自己,终点似乎就在眼前了。但是秋季疫情反弹,特朗普所说的新冠有一天会“奇迹般地”消失很明显是一个完全假想的“终点”。当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个无聊的冬天时,那个假想的终点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该如何应对没有终点线的比赛呢?好消息是,抛弃幻想可能会有所帮助。
在一项研究中,志愿者们被要求以预定的配速跑步,志愿者们之间并不是比赛的关系。实验过程中告诉了一部分志愿者们要以这个速度保持多久,而并没有告诉其余的志愿者们。那些不知道终点的志愿者们心率相对更低,报告中的主观感知努力程度也相对更低。他们的大脑活动也从高能量的执行功能区域转换到了脑袋一份空白的状态。换句话说,当我们适应这种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时,我们的身心都会进行一定的调整。

埃塞克斯大学的研究员Dominic Micklewright进行了一项特别有趣的研究,给自行车新手和老手各配备了眼动追踪装置,让他们进行16公里的计时赛,以研究他们靠什么反馈源来调整配速。新手们主要关注自己还剩多少距离,当他们接近终点时查看的频率越来越高。而老手们则主要关注自己的速度,整场比赛过程中查看的频率大致相同。换句话说,新手关注的是终点和距离终点的距离,而老手则关注自己当下时刻的表现。
Van Deren是在37岁的脑部手术后才开始参加比赛的,这场手术使得她的颞皮质永久性受损,损害了她追踪时间或距离的能力。对于普通跑者来说这可能是一种缺陷,但在超长距离跑比赛中,这简直是一种超能力。她曾经开玩笑说,“可能我已经跑了两周了,但如果有人告诉我这只是比赛开始的第一天,那我可能会想,‘好吧,让我们开始吧!’”

专业超马选手Diane Van Deren的不幸经历恰好给自然实验提供了条件,从中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事实证明,如果你问自己“我还能继续吗?”而不是“我能跑到终点吗?”那你可能更容易能给出一个坚定的回答。这就是面对隔离版超级后院线上超马以及类似事件的方法。
“下一轮,永远是下一轮,”法国跑者Guillaume Calmettes接受《卫报》采访时这么说,他在2017年赢得了一项类似赛事(非线上)的冠军,一共在59个小时内完成了59轮比赛。“你永远不会被剩下的距离所压垮,因为根本不知道还要跑多远。”

8月22日,跑者们戴着口罩参加了在法国西部La Pommeray举行的Trail des Moulins比赛。法国因新冠疫情而实施的第一轮封锁措施在比赛前的几个月结束了,但到了冬天又将开始新一轮的封锁。
活在当下。这句话听起来的确有点陈词滥调。尽管如此,终点预期理论用在这里非常贴切。处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如果没有一个截稿日期,我永远都没法开始写文章。
生活,如果你真的想拼一拼的话,那么生活本身就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佛教的五戒鼓励我们定期思维人固有的生命终点。虽然知道人固有一死,但是计算生命剩下的时间会让人麻痹,而且人生无常,我们也无法了知未来。
我和所有人一样密切地关注着疫苗的新闻。即使你认为疫苗试验会在安全性和功效方面不断传来好消息,但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生产和分销挑战。我可能在今年秋天前都不会抱有期望。因为根据终点预期理论中的各种情况,最糟糕的情况是,当你快跑完原定的回合准备从跑步机上走下来时,实验人员说:“哈,开玩笑,你得再继续跑10分钟!”那个时刻是感觉最痛苦的时候。真正的问题在于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而不是你正面临的一切。
最后剩下的对手没有准时出现。然后他又跑了一轮锁定了胜局。根据官方比赛的规则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Wardian的妻子让他继续参赛时他的顿悟。他后来又跑了19圈,直到第63个小时的比赛开始时,Wardian问自己能否继续跑下去,但赛事组织者拒绝了。“他们拒绝了我的请求,我感到很沮丧”,他后来接受《体育画报》的采访时说。“我当时想,见鬼!因为我觉得自己至少在那个时候身体和心理状态都很好,还能继续跑。”

 跑野大爆炸
跑野大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