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记忆与雅典帝国主义 雅典的公共精神是如何败坏的

希罗多德《历史》犹如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悠远且深邃,它时而悄无声息、一马平川,时而波涛汹涌、奔腾呼啸。希罗多德笔下不断涌动的“故事流”,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之间从容切换,令读者目不暇接,甘之如饴,欲罢不能。这部史诗般的“故事之河”既有支流也有干流,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结构复杂且彼此关联的“流域系统”:其中的“支流”即著作家间或转移话题追根溯源,如王朝世系、民情风俗、地缘风物,而“干流”则是波斯的崛起与衰落,即从前547年吕底亚遭遇灭国至前478年薛西斯远征希腊失败,前后持续正好七十年时间,这也是之后雅典帝国的生命周期。
《历史》旨在探讨希腊人与异族人之间战争的起源,希罗多德的写作对象无疑首先是希腊人,更具体说是雅典人,但他不是正面描述希腊,而是以异族人(吕底亚、爱奥尼亚、波斯)的视角反观希腊的。在仔细研读希罗多德之前,现代读者往往会本能地认为,希腊人叙述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尤其是在希腊人战胜波斯之后的年代里,探索这场战争的起源,必然要粉饰希腊人的壮举,因此难免会受到所谓希腊人立场甚至偏见的宰制。然而,这一所谓的“常识性”臆断却大大低估了古代著作家过人的视角转换和换位思考能力,超越自己所置身其中的文明经验,对“他者”保持高度的智性上的同情,同时以超越式的智识洞见反观“自我”,希罗多德堪称典范。
除了一开篇吕底亚僭主克洛伊索斯与雅典人梭伦之间的虚拟对话外,《历史》中涉及希腊尤其是斯巴达和雅典时,往往依照叙事线索循序展开:克洛伊索斯在攻打居鲁士之前,神谕要求他与希腊人当中最强大者结盟,克洛伊索斯遂派遣使者调查希腊诸邦的实力状况,这就自然引出了希腊人中当时最为突出的两个城邦,即斯巴达和雅典,这两个民族的历史源流、政治制度便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克洛伊索斯最终选择与斯巴达结盟,但由于斯巴达忙于与邻国阿尔戈斯人之间的战争,原计划支援克洛伊索斯的军队出发的行程因此被延误,终在斯巴达援军达到之前,吕底亚首都被居鲁士攻陷。
希罗多德将读者的目光第二次引向希腊,是在伊奥尼亚人起义(前499年)前夕,这场起义旨在团结该地区各城邦联合叛离波斯帝国的统治,起义的主要发动者是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他亲自前往希腊请援,在请求斯巴达支援遭拒之后,阿里斯塔哥拉斯遂转向雅典,此前雅典爆发革命,皮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统治被推翻,阿尔克美昂家族的克里斯提尼在斯巴达的支持下夺取政权,此后雅典国力不断上升,在此处,希罗多德用了大量篇幅对雅典的内政外交处境做了非常仔细的描述。
在雅典公民大会上,阿里斯塔哥拉斯慷慨陈词,以各种空头许诺利诱雅典人,最终如愿以偿,雅典派出20艘舰船援助伊奥尼亚人,波斯陪都萨迪斯被付之一举。虽然此次反叛最终被波斯军队镇压,但这一事件从此成为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积怨的开端,波斯与希腊之间的战端也由此开启:在巩固帝国对伊奥尼亚人统治的同时,远征希腊,惩罚雅典人的罪行,进而消除其对波斯帝国边疆的威胁,被正式提上国王大流士的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希罗多德行文也至于第六卷,大流士远征前夕希腊世界的权力格局、斯巴达和雅典两大城邦各自的内政外交,希腊与波斯之间的马拉松战役,构成了本卷叙事的主要议题。
波斯在马拉松平原的惨败非但未遏制大流士远征希腊,反而进一步激发了波斯大王征服希腊的雄心,大流士壮志未酬身先死,远征希腊的重任最终交给了新继位的薛西斯,波斯与希腊之间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从此拉开帷幕。随着薛西斯数百万远征军不断逼近,是团结御侮捍卫自由?还是主动投诚以求自保?即便是斯巴达和雅典,它们彼此之间就如何备战也发生巨大分歧。从火烧萨迪斯到兵败马拉松,战争的强度和规模不断升级,希罗多德这部伟大的战争史诗最终在温泉关、萨拉米斯、普拉提亚、米卡列被推至最高潮。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希罗多德将有关希腊的场景穿插在波斯帝国扩张的主题叙事序列之中,若将这些片段对接起来,其所呈现的将是一幅关于希腊世界历史的完整画卷。对希腊人来说,波斯战争对希腊世界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雅典在战后年代的迅速崛起,将成为改变希腊人政治生态的关键,雅典人在这场大战中的战争经验和战争记忆,在雅典人的精神世界留下了深刻烙印,战后新帝国的国民心态、雅典人的言谈和行为方式,都能够在波斯战争中找到其思想源头。
对一般读者来说,一提到古希腊,脑海中浮现出的不是深邃的哲学、机智的戏剧、刚健的竞技赛会,就是共和城邦的有机整体、城邦公民的美德懿行,以及以“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为旗帜的民众对城邦公共事务的持续关切和参与……。然而,上述种种更多地是希腊尤其是雅典著作家智力创造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尽管不失其永恒的智性光辉,但现实的城邦政治世界绝非“理想国”的对应物,它远非充满哲学和诗歌的和谐田园。
事实却是,在希腊世界,城邦之间战争频仍,彼此虎视眈眈,城邦集体经常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领土被觊觎、民众遭奴役的悲惨时有发生;而在城邦内部,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内讧不断,城邦时刻有可能滑入内战泥潭而无法自拔,城邦政权经常易手,政体频繁更迭。
哲学家探讨城邦正义的可能,立法家寻找能够消弭城邦内讧的法律手段,通过合适的政体设计实现城邦长治久安……,诸如此类的努力恰恰折射出现实的城邦政治世界,不是和谐的田园,而是潜在的或显在的政治角斗场,这一战场始终弥漫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血腥斗争。“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正义就是助友攻敌”,“不正义的事只要干得大,是比正义更有力,更如意,更气派”、“不正义既明智且有益”……智术师色拉叙马霍斯的这种“常识性”概括,无疑是城邦政治处境最为直观的观念上的反映。
在希腊诸城邦中,雅典城邦内部党争内讧不断,其为害既深且远:贵族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平民在忍无可忍,便揭竿而起,铤而走险;贵族傲慢贪婪,平民怨恨嫉妒,双方势同水火,彼此虎视眈眈,城邦政事废弛,公益不存,乖戾之气弥漫朝野,为此,时任执政官(前594年)的梭伦为此悲叹道:“我举目四望,满怀悲伤地看着。爱奥尼亚人最古老的家园被蹂躏得毫无生机。”
梭伦上任伊始,便颁布新法,变革政体,推行新政,旨在消除分歧,弥合党争,颁布“解负令”,减轻民众负担,根据财产划分社会等级,同时依照等级分配公职,赋予政治权利,……梭伦将新法刻于“库尔贝斯”(kyrbeis),立于王者柱廊(Basileios Stoa),宣誓百年不变,冀望雅典从此摆脱纷争,协和城邦,国泰民安。梭伦力图超越派性,弥缝裂痕,却两头受气,无论是匹夫匹妇,还是寡头权贵,都对他横眉冷对、恶语相加:贵族因新法而受损,自然心生怨怼;平民因新法有所得,却贪心不足,得寸进尺。
为确保新法落地,消除党争,梭伦本可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以僭主意志支撑共和法权,但他最终拒绝僭主位,转而远走海外,自我流放,云游四方,这正是希罗多德在《历史》一开篇即安排梭伦与克洛伊索斯的那场对话的历史依据。据普鲁塔克,梭伦晚年一度计划完成一部关于“已沉沦的大西洲”的故事或寓言的巨著,其意在讽喻雅典,无奈年世已高,精力不济,只好放弃,后世哲人柏拉图著《克里蒂亚》,重拾这则有关“已沉沦的大西洲”的寓言,其意味和关怀可谓既深且远。
雅典城邦内讧并未因梭伦立法而稍有缓解,梭伦离开后,雅典党争变本加厉,之后雅典国内局势持续动荡近五十年之久(前593-前546),最终,极端民主派(即“山地派”)领袖皮西特拉图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希罗多德叙事至克洛伊索斯攻打波斯前夕派人前往希腊寻找盟友之时,将目光转回希腊,这时的雅典正是僭主皮西特拉图初次当政,希罗多德这样写道:“雅典人在当时雅典的僭主、希波克拉底之子皮西特拉图的统治之下,正在遭受悲惨的压迫,内讧不断。”(I-59)皮西特拉图的夺权之路险象环生,“两落三起”,且几度命悬一线:两次被逐(前559/前556),最终在前546年第三次入主雅典,从此雅典政局才开始趋向稳定。
皮西特拉图保留了梭伦的大部分立法,在位期间勤政爱民,雅典市政建设全面提升,民生事业全方位改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如《荷马史诗》的编纂),为此,希罗多德写道:“他原封不动地保留此前已有的各种官职,也不变更任何法律。他根据既有的制度管理城邦,他的政策措施不仅是贤明的,也是有益的。”僭主去世(前527年)后,其子希皮亚斯继位,二代僭主延续乃父一贯的执政作风。而对于皮西特拉图僭主家族的统治,亚里士多德评价说,表面上这个家族在雅典推行的是僭政,其实际表现却与宪政无异。公允来说,雅典国势日隆,乃至后来的崛起,僭主家族的统治功不可没。
然而,雅典城邦在僭主家族统治下的这一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终因前514年那场著名的“弑僭”密谋戛然而止,事实上的僭政一转而成虐政,直至四年后被彻底推翻,后学修昔底德对该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仔细考证。希罗多德的叙事进行到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格拉斯到希腊请援,雅典当时正值僭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时期。由阿里斯托吉吞与其小情人哈摩狄乌斯策划的这场暗杀活动,本是一场因性嫉妒而引起的私人仇杀,却被后来的夺取政权的阿尔克麦昂家族标榜为“民主革命的先驱”,为他们树碑立传,诗词歌赋,纷纷将他们歌颂为“自由”之男神,雕刻大师安特诺尔(Antenor)为两人雕刻纪念像,立于雅典广场供人们瞻仰。
在以克里斯提尼为首的新的民主政权的官方历史教科书中,这起本来令人啼笑皆非的阴谋,却被传播为一场充满情怀的浪漫革命爱情剧,而“僭主”、“僭政”、“皮西特拉图家族”从此成为“专制”、“暴政”的代名词。实际情形却是,这场“弑僭”闹剧本身非但未直接推翻僭主家族的统治,希皮阿斯因此反而变得偏执多疑,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对任何可能与暗杀活动有关的人格杀勿论,这就在事实上使本来一直推行善政的僭主政权一转而变得空前残暴,直至四年后,即前510年,一直流亡在外的阿尔克麦昂家族在斯巴达的鼎立支持下,最终推翻僭主家族统治,希皮阿斯辗转流亡波斯,并跟随薛西斯远征军攻打希腊,力图复辟,这当然是后话。
僭主统治的被推翻,雅典再度陷入内乱,以克里斯提尼为首的阿尔克麦昂家族与以伊萨哥拉斯集团展开新一轮政权争夺:期间,克里斯提尼先发制人,采行一系列带有民主色彩的新政举措,迎合普通民众的需求,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威:例如他重新设计雅典行政区划,推行由十部落、三十组德莫(demos)、三一区,以五百人议事会取代四百人议事会,以取得平民的支持;克里斯提尼还推行陶片放逐法,据亚里士多德说,此法最初是为希皮阿斯的外孙希帕库斯“度身定做”的,而此后该法名义上是为防止野心家复辟僭政,实际上却沦为政客借以剪除政敌的堂皇利器。
眼见克里斯提尼日益得势,伊萨哥拉斯当然不甘示弱,转而寻求斯巴达的支持,而斯巴达也力图另立伊萨哥拉斯为僭主;与此同时,克里斯提尼则向波斯人寻求支持。这一时期由于雅典内讧不断,斯巴达因之获得了干预雅典国内事务的绝佳时机,期间斯巴达先后四次入侵安提卡,其中“两次是作为敌人来到这里的,两次是来为雅典平民提供有益帮助的。第一次入侵是发生在他们在麦加拉建立一个殖民地的时期,把这次出征放在科德鲁斯统治雅典的时期肯定是确当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是他们从斯巴达出发,前来驱逐皮西特拉图族人;第四次也就是这一次,克列奥蒙尼统率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队进抵埃琉西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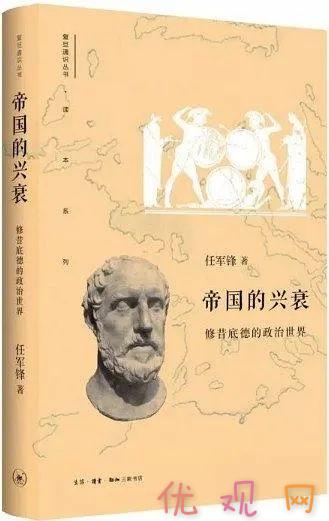
《帝国的兴衰》
此后雅典内政渐趋平定,国势也不断增强,而雅典与邻国之间的战争也日趋频繁,雅典先后与波奥提亚人、卡尔基斯人、底比斯人、埃吉那人、阿尔戈斯人发生激烈战争。城邦世界时刻面临的生存危机使雅典人认识到,城邦的实力才是一切,所谓“正义”,乃是强者的特权,弱者从来就没有资格要求“正义”。
雅典人曾经遭受强权的任意宰制,到自己有朝一日获得强权,同样可以理直气壮地宰制别人。雅典人的历史记忆使他们坚信,政治世界运行法则从来就是:强者理当颐指气使,弱者自当承受愉快,修昔底德笔下发生在前416年即雅典远征西西里前夕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弥罗斯人的辩论”,正是雅典民族生存记忆长期形成的精神积淀,对雅典人来说,政治世界从来表现为强者与弱者、胜利者与失败者、敌人与朋友、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对立:“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的范围以内扩张统治的势力,这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制造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是最早使用这个规律的人。我们发现这个规律老早就存在,我们将让它在后代永远存在。我们不过照这个规律行事,我们知道,无论是你们,或者别人,只要有了我们现有的力量,也会一模一样地行事。”
波斯人的两次入侵,雅典人所遭遇的灾难和屈辱,在很大程度上印证并强化了雅典人的上述观念主张,而这恰恰构成了战后雅典帝国主义的精神基础。
雅典:从委曲求全到扬眉吐气
希腊各城邦内部政局持续动荡,城邦之间相互敌视,彼此觊觎,而东面又时刻面临庞大的波斯帝国的威胁,从公元前522至前424年,在波斯三代君王(大流士、薛西斯、阿塔薛西斯)当政近百年的时间里,希腊世界深受其害,由于希腊人内部的长期不和,这就给波斯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为此,希罗多德这样写道:“在波斯的这三代国王当政期间,……希腊所遭受的灾祸比大流士之前的20代所遭受的灾祸还要多。这些灾祸的一部分是来自波斯人,一部分是来自强国之间的争霸战争。”
前490年,大流士的远征舰队在流亡僭主希皮亚斯的带领下,在马拉松平原登陆,妄图进一步入侵雅典。雅典人闻讯,派兵开往马拉松,同时派遣长跑能手斐迪皮德斯(Phidippides)前往斯巴达请援:“拉栖代梦人啊,雅典人请求你们赶快发兵援助他们,不要眼看着全希腊最古老的一个城邦遭受异族人的奴役。如今爱利特里亚已经受到了奴役,一旦失去这座名城,希腊就会进一步遭到削弱。”然而,作为当时希腊世界的“龙头老大”,斯巴达对雅典势力的日趋增长早就心有余悸,一直想方设法削弱之,如蓄意挑唆底比斯与雅典之间的矛盾,这次波斯人入侵,斯巴达故伎重演,以月历不时为由,拖延援军出发日期。
而在这场关涉整个希腊世界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只有普拉提亚人给予雅典以军事援助。所幸的是,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中完胜波斯,使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士气和自信大为提升,而在此之前,“希腊人但凡听说波斯人的名声,就会感到胆战心惊。”作为马拉松战役的核心力量,雅典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在这次战役中,身为波列玛克的卡利马库斯英勇作战,壮烈牺牲;塞拉西劳斯的儿子斯特西劳斯,时任雅典十将军之一,也死于敌军之手;攸佛里昂的儿子库奈吉鲁斯(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兄弟),他在用手抓住敌人船尾时,手被敌人的斧头砍掉,而命丧战场,雅典其他许多知名人士也都阵亡了。”(VI-114)斯巴达人的“援军”姗姗来迟,他们到达马拉松时,战斗早已结束,但他们也不忘顺路去亲眼目睹一下风闻中的天兵天将——波斯士兵,即便是一睹波斯人的尸首也算开了眼界。
马拉松战役遭遇惨败,波斯自然不会善罢甘休,薛西斯发动数百万大军第二次远征希腊,无疑是对希腊人团结御侮决心的最为严峻的考验。当远征军到达马其顿,薛西斯深知希腊各城邦之间积怨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便派使者前往除斯巴达和雅典之外的所有城邦招降,包括色萨利、洛克里、阿凯亚、底比斯在内的北希腊和中希腊地区相继向波斯投诚,转而帮助异族人攻打希腊,而许多尚未投诚的城邦则选择袖手旁观,面对占据压倒优势的波斯军队,他们毫无信心,充满恐惧,“希腊大多数城邦都不想卷入战争,而是正热衷于投到波斯人的那一边去。”
而处于希腊腹地的阿尔戈斯人鉴于强邻斯巴达的威胁,暗中与波斯通款,以提出与斯巴达分享联军统帅权遭拒为借口,堂而皇之地按兵不动,也就变相帮助波斯人。希罗多德指出,对阿尔戈斯人来说,若从城邦私利考虑,显然是一种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这与希腊许多城邦在异族人的侵略面前的举动相比,阿尔戈斯人的行为“还不能说是最无耻的”。
希腊联军派使者到西西里请援,叙拉古僭主格隆漫天要价,要求除非斯巴达交出统帅权或至少雅典交出海军指挥权,才可能派兵增援,格隆心里当然知道对方不会让步,遭到拒绝后,格隆便派使者携带大量金钱和通款条件前往德尔斐,观望战事进展,“如果异族军明显占据优势,那么就把那些金钱交给薛西斯,同时代表格隆统治下的领土,献上‘土和水’。——如果希腊人获得胜利,那么就把这些金钱如数带回来。”
克基拉城邦的表现则要爽快得多,口头上答应驰援,但援军却蓄意滞留中途,首鼠两端,作壁上观;克里特也以神谕不利为由,未派一兵一卒;……。温泉关战役,斯巴达国王及其麾下的三百勇士的壮举固然鼓舞了希腊人的士气,也在客观上牵制了波斯军队的前进步伐,但毕竟未能在军事上真正削弱波斯人的锐气。
大敌当前,无论是海军实力还是海战经验,雅典都首屈一指,然而,当有人提议将海军指挥权交给雅典人时,却遭到同盟者的一致反对。雅典人顾全大局,避免因为指挥权而争吵不休,影响抗敌大计,便主动放弃对海军指挥权的要求。希腊联军本可以在波奥提亚抵御来犯之敌,然而由于斯巴达这时已经开始考虑自己后方的安全,联军不顾雅典人的反对,迅速撤退至萨拉米斯,这就等于在战术上将安提卡完全暴露在波斯军队的锋芒之下。波斯人在雅典大肆烧杀劫掠,神庙遭到洗劫,卫城被付之一举。
面对此情此景,雅典将军泰米斯托克利心急如焚,力图阻止联军将帅放弃萨拉米斯、转而退守科林斯地峡的动议,他得到的却是同盟者的嘲讽:既然雅典已被异族人攻克,雅典人已经沦为亡国之人,丧家之犬。眼看联军议决退守地峡,泰米斯托克利急中生智,利用反间计促使薛西斯提前进攻萨拉米斯,最终迫使希腊人在萨拉米斯迎击来犯之敌。萨拉米斯海战最终成为希腊人扭转战局的转折点,不仅挽救了雅典,也拯救了整个希腊。
雅典作为“希腊的救星”:新帝国的战争记忆
波斯战争,希腊人一度处于全线崩溃的边缘,最终有如神助,扭转乾坤,反败为胜,令波斯大军折戟沉沙,不可一世的薛西斯最终铩x羽而归。在几场扭转战局的战役中,如马拉松、萨拉米斯、普拉提亚,雅典将军米太雅德、阿里斯提德、泰米斯托克利足智多谋,指挥若定,由于地缘上被直接暴露于抵抗波斯的前线,雅典人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领土两度遭波斯蹂躏,百姓流离,寄人篱下。
在战后希腊世界,雅典作为新的霸权国家,经常遭人侧目甚至敌视,但希罗多德还是大胆站出来,明确肯定了雅典在战争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希罗多德看来,即便将雅典人视为“希腊的救星”也毫不为过,他写道:“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一个意见,虽然大多数人是不喜欢这个意见的。但是,只要我觉得是真知灼见,我决不会避而不谈。假如雅典人被迫在眉睫的危险所吓倒,从而离弃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他们虽不离开,却留下来向薛西斯投降,那么,肯定就没有人力图在海上抗击波斯人了;而如果没有人在海上抵抗波斯人,那么我认为在陆地上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无论伯罗奔尼撒人修筑多少条横贯地峡的城墙来保卫自己,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还是会离弃他们,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毫无疑问,随着同盟者的城市被波斯舰队一一攻陷,他们的同盟者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不得已,都要离弃他们。这样,孤立无援的拉栖代梦人,就势必得单独对敌鏖战一场而光荣地覆灭。这将是他们的命运;不然,在他们看到希腊的城邦一个接一个地都归降了波斯人之后,他们最终也会和国王薛西斯缔约求和了。
所以,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发生哪一种,希腊都将为波斯人所征服。我无法理解的是,既然国王掌握着制海权,那他们在科林斯地峡上修筑城墙究竟还会有什么用处。既然如此,如果说雅典人是希腊的救星,那就的确是一个真知灼见了。雅典人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哪一方得到他们的支持,哪一方就会得胜。雅典人所抉择的是希腊应当保持自由;也正是他们,激励尚未归降波斯人的那些希腊人,而且正是这些人,在诸神的庇佑下,击退了入侵者。”
雅典曾经是“希腊人的救星”,将来理应成为“全希腊的主人翁”,在希腊世界树立“雅典治下的和平”,雅典人关于波斯战争记忆,成为雅典帝国国民的精神支柱,而随着战后雅典国力不断增强,雅典人的上述信念日趋坚定不移。雅典与斯巴达开战前夕,在修昔底德笔下,那位普通雅典人在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上的慷慨陈词,正是上述心态的集中反映:“……我们要提到波斯战争,提到你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事件,纵或你们也许因为经常听到这个故事而感到厌倦了。在当时的战争中,我们为着共同的利益,冒着一切危险;你们也分享了这一切的利益;……我们在马拉松抵抗波斯人到底,我们是单独对付他们的。
以后他们再来进攻,我们在陆地上不能抵抗他们的时候,我们和所有的人民都登上船舰,在萨拉米斯交战。就是这次战役阻止了波斯人,使他们不能航海来进攻伯罗奔尼撒,使他们不能一个一个城市地破坏;……我们所表现的勇敢是无比的。陆地上没有人来援助我们;直到我们的境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被奴役了,而我们自愿放弃我们的城市,牺牲我们的财产;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共同事业中,尚且不肯遗弃我们其余的同盟者,……我们登上船舰,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对于你们不早一点来援助,我们毫无怨言。……我们的后方是一个已经不存在了的城市,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前进,为着这个似乎不可能恢复了的城市,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因此,我们和你们联合在一起,不但挽救了我们,同时也挽救了你们。”
随着波斯战争的胜利,雅典在希腊世界名声大躁,随着雅典国家“硬实力”的提升,其“软实力”也不断增强,雅典民主制度成为许多希腊城邦竞相效仿的典范,雅典俨然成为希腊世界的文教中心。战争锤炼了雅典人的决心和意志,也使他们找到了真正适合雅典人的强国之道:即建立强大的海军,以确保雅典在东地中海的新霸权,对波斯势力构成持久的抑制作用。先前令希腊人闻风丧胆的波斯军队,原来不过如此,他们并非传说中的神一样的存在,一样的肉身凡胎,战争使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开始重新认识自我,雅典人从这场战争以及对自己在战争中的壮举的不断追忆甚至渲染中获得了空前的自信。
正如当初克洛伊索斯发动的那场针对居鲁士的战争,波斯战争结束了一个帝国,也催生了一个新的帝国。雅典人用旧帝国的瓦砾,建立起一座新帝国的大厦。恰如伯里克利在那场著名的国葬演说中所说的,“尤其是我们的父辈,更加值得我们歌颂,因为除了他们所继承的土地之外,他们还扩张成为我们现在的帝国,他们把这个帝国传给我们这一代,不是没有经过流血和辛勤劳动的。”
维持帝国的庄严感和帝国公民的优越感,必须时刻将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因而必然会遭到他人的嫉妒甚至仇视,这在以伯里克利为代表的雅典政治家眼里,正是经营帝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新帝国公民必须对这种嫉怨勇于担当,受之愉快。在雅典人看来,帝国为了自身的安全、荣誉和利益,采取非常手段是再正常不过的举措,这不是雅典人的发明,之前的斯巴达、波斯都是这么干的。雅典人只不过是奉行久已形成的帝国统治法则罢了。
《历史》叙事临近收尾,希罗多德突然岔开话题,讲到一位名叫阿腾巴列斯的波斯人与居鲁士大帝的一则对话:波斯人推翻米底王国后,阿腾巴列斯极力劝说居鲁士将波斯人迁出他们长期祖居的山地,寻找更为平坦富饶的土地居住,这是任何由弱变强的民族的必然选择,波斯从当初的那个偏安一隅的小部落如今成长为一个威震整个亚细亚的大帝国,此时不迁更待何时?居鲁士说波斯人可以照建议的去做,但与此同时他警告波斯人说:“一旦这样做了,就不要再指望继续担当统治者,而要准备成为受别人统治的臣民——适中的土地养育宽厚的人民——但没有哪一块极其丰产的土地上,同时会养育出勇武的战士。”波斯人为居鲁士的智慧所折服,最终听取了居鲁士的警告:“他们宁肯居住在崎岖的山地上担任统治者,也不愿居住在平坦的良田上充当别人的奴隶。”
贫穷而得享自由,奢侈而遭受奴役。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希罗多德叙事结尾处的这一意味深长的寓言式对话,与开篇第一卷中那位名叫桑丹尼斯的吕底亚人对克洛伊索斯的劝谏如出一辙,而桑丹尼斯与结尾处的居鲁士一样,也是一位智慧之人。当克洛伊索斯跃跃欲试准备攻打居鲁士时,桑丹尼斯进谏说:“国王啊,你准备去攻击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穿着皮革制的裤子,他们的衣帽也都是皮革制的;他们的食物并不是他们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那贫瘠不毛的土地上生产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而且他们平常不饮酒,只饮水;他们那里没有无花果,也没有其他什么好吃的东西。这样,如果你果真征服了他们,他们既然一无所有,你又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呢?反之,如果你被他们征服的话,你仔细想想看,你将失去多少好东西啊。他们一旦品尝到我们的好东西,就会紧紧地抓住这些东西,我们再也无法叫他们放手了。至于我,我要感谢诸神,因为诸神没有让波斯人想到要来进攻吕底亚人。”
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战争中大获全胜,占领玛尔多纽斯的营地,联军统帅波桑尼阿斯看到那金银镶饰的帐篷、五颜六色的遮帘、华贵的卧榻、金银餐桌以及波斯人丰盛的大餐,真是大开眼界,心情无比愉悦,同时他命随军厨师做了一顿斯巴达式晚饭。不比不知道,一比可真是吓一跳,同样是吃的,差距俨如天壤。波桑尼阿斯将他手下的将领们叫来,大笑道:“希腊人啊,我派人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是想要你们看一看波斯人的领袖是多么愚蠢,他每天享受着这样豪华的盛宴,却非要到我们这里来抢夺我们这点可怜的伙食。”
波斯人摧毁了吕底亚,却成为吕底亚生活方式的奴隶;希腊人打败了波斯,却最终被波斯人的生活方式征服。对帝国来说,其势力如日中天、富庶奢华之日,或许正是其民众走向萎靡苟且、民情日趋颓坏之时。这应该是伟大的希罗多德留给我们的又一意味深长的精神教诲吧!

 杨聪雷博士
杨聪雷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