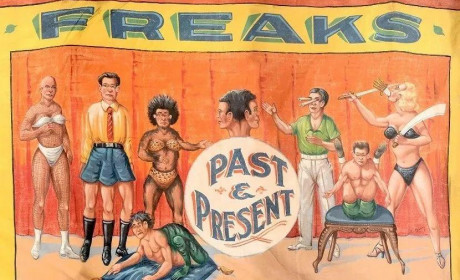奇异的人体悬挂世界
利维坦按:或许从实用主义者看来,他首先会问:人体悬挂能给我带来什么?毕竟,打耳洞、穿鼻环、文身都有可以见到的结果。当然,对于不能接受这种活动的人而言,“疼痛”或许是他们最无法理解的。又或者,在另外一个宗教文化环境中,这一现象又能得到自洽的解释。不过,本文试图告诉你,即便不是为了追求宗教上的意义,人体悬挂也具有某种精神冥想的含义。
本文或许包含令你产生生理或心理不适的内容或图片
请酌情考虑是否继续阅读
“深呼吸。在你呼气时,我会用针穿过你的皮肤。”
希尔·科切蒂(Cere Coichetti)这样说着,克里斯蒂娜·巴帕托(Christina Barbato)闭着双眼。接着,他将绳锁链挂在她背后的钩子上。巴帕托抬起头来看着科切蒂,他面带宽慰地微笑。在她释放出自己感觉舒适的明确信号后,他拉起了绳子,她升到了空中,拉着她的只有她背上的绳索。

希尔·科切蒂(中)在丽兹·道吉(Liz Dodge)、格里琴·汉尼尔(Gretchen Heinel)和埃里克·安德森(Eric Anderson)的帮助下,将克里斯蒂娜·巴帕托吊起于瀑布之上。
人体悬挂是一项有5000年历史的传统活动,它起源于印度。印度教教徒会在一场名为卡瓦第(vel kavadi)的宗教活动中将彼此悬挂在半空中,以此表示对神灵穆卢甘【Murugan,编者注:又名室建陀(Skanda),印度教的神祇,为湿婆神与雪山神女的儿子,是智慧之神财神象头神的兄弟,形象是一名俊俏挺拔的少年,也是战神。据说佛教的知名护法神韦驮天,原型即是室建陀】的虔诚。在美国,曼丹族原住民部落在一年一度的奥基帕节(Okipa)的最后一天也会进行类似的悬挂活动——这个仪式是年轻战士的勇者测试。

希尔·科切蒂
现代人体悬挂之父名叫法基尔·穆萨法尔(Fakir Musafar),他在南达科他州的一片原住民居住地长大,并对奥基帕仪式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所主张的人体悬挂形式并不具有太强的宗教意味,反而更像是从日常问题入手,净化人身体和心灵的一种精神冥想。
自从2001年初,一位同行的身体修饰艺术家朋友向希尔·科切蒂介绍了人体悬挂这一行为,他便开始练习。他的初次悬挂姿势被称作“超人”,用了10只插入整个身体的钩子。
“我只是想看看,我是不是勇敢到能尝试这样的事情,”科切蒂回忆道,“这看起来是世界上最疯狂又痛苦的事情,但当我升入空中的那一刻,我的想法与这种感受截然相反。我觉得一切消极的情绪都被倒出了我的身体,直到最后只能感知到一尘不染的喜悦。”

格里琴·汉尼尔:“我第一次尝试人体悬挂是在我朋友纽约的公寓里,我呈莲花体式被吊起来。(悬挂的钩子为三组:第一组在背上,第二组在膝盖周边区域,第三组在腿肚子的肌肉上)——这是我这辈子感受过的最强烈的疼痛感之一。但是,如果拿走小腿上的钩子,仅仅靠背上钩子的支持摇摆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平静。在我和我的朋友都被挂起来后,我们就在这个有些疯狂的高度上‘闲逛’。我们做了这件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谬的甚至不太可能的事情,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从不同角度看待我生活中的很多事——很多困境与挣扎并没有达到不可能克服的地步。”
科切蒂成立了“勇者测试”的纽约分支,从穆萨法尔的一位弟子那里学习悬挂技术。在他和他同伴的努力下,人体悬挂的团体已经从寥寥几位习艺者,拓展壮大到遍布全国的数千人。后来,他成立了一个名为“白旗”的组织,参与者要出资以支付物资成本,但是“白旗”不具有盈利性;科切蒂相信每个人都能体验人体悬挂,他们欢迎每一个想来的人。

安置在宾西法尼亚的森林中用于悬挂的绳索。

参与者背部放置钩子的地方,留下了十字型的痕迹。
“我曾思考这项活动能为人类带来什么,因为我看到了它带给我的东西。我意识到它应该被分享,”科切蒂说,“我想和别人分享这种无与伦比的感受。”
“给身体穿个孔并不会造成很大伤害——实际上这取决于穿孔的位置,它能给人造成的伤害最多也就和医生给你打一针一样大。当一个人被吊起的时候,我会和被挂起来的人讲明白,他们被挂着的地方将会体验到灼烧和热量迸发的感觉,这种感觉会在你被抬到空中的过程中不断加剧,但大概过30秒就会自行消失。”

图为在背上穿孔后,以“超人”体式被挂起来时,丽兹·道吉的反应。这个姿势要用十个钩子:背上有六个,双腿上各有两个。

前臂悬挂中,已经就绪的钩子。
我在担任科切蒂婚礼摄影师时与他相识,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在他向我介绍人体悬挂的理念后,我立刻就被吸引了。我想亲眼目睹这样的场面,他便邀请我同去一次为期四天的野营,野营的目的地是宾夕法尼亚州威廉姆斯波特,同伴还有他从人体悬挂组织中结识的12位朋友。小组中的每个人立刻对我表示了欢迎。在行程的前两天中,我看到了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新朋友们将钩子刺入自己的身体,悬停在森林里孤立的瀑布上。

埃里克·安德森:“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通过肉体与灵魂考验,才能真正地与上帝同在……才能真正地与自我和他人联系……你总要同别人一起经历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才能彼此在个体与灵魂层面更加接近。”
我们带的绳索、悬挂装置和露营装备总计质量超过400磅。整个小组都参与了将绳子挂在树上的过程,这一过程结束后,克里斯蒂娜·巴帕托的第一次悬挂开始了。她凭借背上的两个支点悬挂在瀑布之上。这些年来,科切蒂不断改良的滑轮装置能够使她从站在地面上开始这次体验,并在瀑布上脱离一些支点。巴帕托悬挂的时间大约有40分钟,她像节拍器一样来回摆动,在空中“奔跑”并在空中溅起水花。团队其他人则站在瀑布边缘,科切蒂和他的助手格里琴·汉尼尔抓住绳子,使她保持悬空。

左图为埃里克·安德森悬挂后的背部包扎,右图为装穿孔器具和药物的处置箱。
我们在给身体穿孔用的帐篷附近设置了一个站点,处置箱被紧紧地贴在树上,帐篷里储备有供给的药物以便汉尼尔能用托盘带出。科切蒂带着十二分的谨慎,以确保一切都是无菌的。所有的针和钩子都像在牙医诊室里那样经过高温灭菌。科切蒂的手套磨损得很厉害,但他进行操作的皮肤处总是清洁过的。一旦皮肤清洁后,科切蒂便会打上十字型的小标记以确定钩子的位置,然后,他用力拉扯皮肤,将针穿过身体,并通过螺栓将钩子固定到位。
准备就绪后,每个人都走向水边,在这里,科切蒂把绳锁链固定在钩子上。一般情况下,悬挂不会在高于80英尺的瀑布上进行,所以科切蒂采取了额外的步骤,用松弛的安全绳进一步控制被悬挂者。

“针刺入皮肤的触感/是仿佛世间万物都已消失”
“与绳索相接那一瞬间的刺痛啊/与地面分离那几分钟的灼伤啊”
“高潮来临/我一无所有/只在阵阵的痛楚中/飞翔”——克里斯蒂娜·巴帕托
将人拉入空中的过程经过了周密的计划和大量的计算。科切蒂从攀岩、舞台装备和建筑等行业中借鉴学习了大量的装置,将绳子固定在树上也用了许多不同种类的绳结。绳索被缠绕多次,以确保没有任何失误的空间。
我们利用梯子爬到瀑布上方树的高点,然后将绳子放下并固定在水边的树上,在这里,科切蒂能够控制住被悬挂者。当然,绳索工具可能会发生故障,皮肤也随时有可能撕裂,这些事情的确偶尔发生。但是,在皮肤真正撕裂之前疼痛往往会加剧,科切蒂也有预防措施和急救药品,以便在不测发生前快速将被悬挂者转移至安全地带。
随着好奇心愈发膨胀,我开始向其他人询问被挂起来时的真实感受。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这些人非常开诚布公。在被对未知事物的恐惧折磨之后,我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做这件事呢?”

左图为连接绳锁链、保持身体悬空的绳索工具;右图为丽兹·道吉戴着“超人”式悬挂所需的所有钩子趴在地上的情景。
最终,当意识到被恐惧和沮丧吞噬可能比人体悬挂本身更令我痛苦后,我在一块岩石上坐了下来,让科切蒂在我的背上消毒、做标记。他和安德森拉扯着我的皮肤并让我深呼吸,两人同时将钩子穿过我的身体,并将它们固定在一起。这个过程出人意料地痛苦,我忍不住叫出了声。针穿过我的皮肤发出了“砰砰”的爆鸣音。
我第一句话是:“我的背上真的有钩子吗?”痛觉是尖锐的,但它在几秒内就消退了。
我们一起走向瀑布,科切蒂将绳锁链固定在我背上的钩子上。当他开始将我送上天空时,他让我想象自己正扛着两个沉重的行李箱,以防止我抬起肩膀。疼痛在此时已经不存在了,只有灼烫的不适感,就像晒伤一样。团队的另一名成员莱拉牵着我的手引导我,克里斯蒂娜·巴帕托为我们弹唱尤克里里。双脚离地后几秒,我就落回了原处,我为自以为自己不能被拉起的想法感到难为情。科切蒂和其它的新朋友们都宽慰我,相信我一定能克服恐惧。于是,我告诉科切蒂把我拉起来并控制住我,再度将我送回空中。他表现得像个向导,以最令人舒适的方式帮助我在进入悬挂前放松下来。他的手拉住绳子的一端,我因此感到很安全。

希尔·科切蒂(右)在笔者首次悬挂身体时宽慰他。(摄影:米卡·哈根)
在我的双脚终于离开地面后,我背部的不适烟消云散,我正在飞翔。我向下俯瞰,看着这些如今我视为家人的人们,其中一些人注视着我第一次人体悬挂的过程,开心得泪水夺眶而出。我在空中拍下了这个团队,然后下来了。当双脚重回地面之时,泪水从我的脸上滑过。身边有一些哭泣声,剩下的都是高声的欢呼,科切蒂双臂环抱着我,我们的距离又近了一些。我在想的全是我如何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就在24小时前我还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切。

“挂在钢钩上在空中左摇右摆,绝对是一件极乐享受。这使我感到自己好像能征服整个世界。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开心,所有的事都更令人愉快,大自然也好像更美了。这一切很难以解释。当你的意志绝对安静下来,真正置身于那个情境之中,万物妙不可言。”——丽兹·道吉

图为野营的最后一天时,埃里克·安德森拿着梯子爬上瀑布顶端,收集树上挂着的绳子的场景。
结束了第一次人体悬挂,我知道我能克服的困难远远超过我为自己设定的心理预期。时间过了一个月,回味这段经历,我发现自己的自信心明显增强。每当我直面挑战、恐惧或阻碍,我便想起我升入空中的那一刻。正如科切蒂解释的那样:“人体悬挂的体验可以有无穷的意味:一次冒险、尝试攻克令人惧怕的任务、一次心灵的体验。我不想去尝试控制这种经历使它成为什么,人体悬挂并不给予你你想要的东西,它给予的是你需要的东西。”

笔者在第一次人体悬挂时为团队拍的照片
补充阅读
人体悬挂的简单历史

图自剧目《22ss项目》
人体悬挂是在人身上临时穿孔,并将其悬挂在大型挂钩上的行为。这是一种可以追溯至上千年前的传统,曾经是为了神圣的、仪式性的目的而被严格执行。
最早被记录的人体悬挂行为发生在大约5000年以前,由虔诚的印度教教徒首创。网站Skin-Artist.com的资料显示,当时“……用身体来超越躯壳的想法在精神和现实生活中都非常流行”,于是印度教的精神领袖用这种方法探索身体和精神间的联系。进行人体悬挂的人将之视作一种苦修,如果一个人能参与越来越高强度的悬挂行为,他对印度诸神的虔诚程度会越来越高。

部落中在背部放置挂钩的人体悬挂。
早期许多印度教徒都会进行人体悬挂,但如今几乎只有印度的萨维特印度教徒才会这么做,他们崇拜湿婆神、穆卢甘神和卡利神。尽管现在印度和斯里兰卡都禁止了人体悬挂相关的节日,但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仍然相信人体悬挂可以带来精神力量。此外,现在东南亚其他地区,如泰国和马来西亚,也有许多人体悬挂活动存在。
美国印第安人的人体悬挂
除了在东南亚有信徒会进行人体悬挂,一些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也有几百年的人体悬挂传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曼丹部落(Mandan Tribe),他们曾居住在密苏里河及其两条支流沿岸,如今生活在北达科他州。在他们一年一度的奥基帕(Okipa,或Oh-Kee-Pa)仪式上,人类悬挂是一项重要内容。奥基帕仪式为期4天,需要所有参与者进行充分的准备和自我牺牲,路易斯和克拉克(Louis and Clark)探险队成员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首次正式记录了这一仪式。在仪式过程中,为了获得他们的神的认可,曼丹部落这种针对战士的训练将紧张到他们的极限,甚至超越极限。参与者不仅会被悬挂很长时间,而且还会经历加重和负担其他压力,最终往往会失去意识。

曼丹部落在奥基帕仪式中的人体悬挂。
现代社会的人体悬挂
自从人类历史开始,极端的仪式一直是世界各地部落文化的核心元素。有趣的是,相距如此之远的两个文化似乎彼此独立地发现了人类悬挂的精神意义。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示,向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进行祈求,人们不惜付出一切努力——这体现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性。所以人体悬挂的传统延续了几千年并在现代社会中真正开始蓬勃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西方国家中,仍然许多修行者将这一过程视作是为了纯粹的精神启示,但此处感谢艾伦·福克纳(Alan Falkner)的工作,许多人还发现了这种行为除精神上以外的好处,比如放松、使头脑平静、发展身体耐力,还将其作为一种吸引人的表演艺术媒介。

图源:MediaZink
艾伦·福克纳对主要人体悬挂的姿势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最常见的人体悬挂姿势包括:
胸部悬挂:挂钩放在胸部,使身体垂直悬挂于地面。
昏迷悬挂:将挂钩穿过胸部、躯干和腿部,身体正面朝上,水平悬挂于地面。这个名字来源于身体摆的姿势——和躺在医院病床上昏迷不醒的人没什么两样。
自杀悬挂:一般挂钩穿过躯干的背部,身体垂直悬挂于地面上。这样姿势因为看上去和上吊自杀的人相似而得名。
十字架悬挂:这个姿势和自杀悬挂的主要区别在于挂钩穿过躯干和手臂的后面,当这样被悬挂时,身体看起来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
超人悬挂:一排挂钩穿过人的身体背部,这个姿势让他们看起来像飞起来的超人。
福克纳(Faulkner)或膝盖悬挂:通过穿过膝盖的挂钩倒挂悬吊者的身体,使他们的头部离地面最近。因为艾伦·福克纳第一次表演而得名福克纳姿势。
复活:在这种姿势下,身体通过腹部的钩子被悬挂起来,弧形悬挂的身体使其看起来就像从坟墓中复活的尸体。
人体悬挂的每个姿势都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往往需要一群熟练的、在人体悬挂上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参与。悬挂者停留在空中的时间越长,准备工作需要的时间越长,包括准备悬吊用品,进行确保安全的步骤(比如一些皮肤上的准备),刺穿身体,插入悬吊钩,以及安装实际悬吊所需的索具。也就是说,如果你曾参与或想要进行人体悬挂,你有可能在装备好之前要等好几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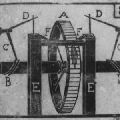 利维坦
利维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