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戏说童年,有色童年成最美好的回忆
今日带着学生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十二三岁的他们对戏曲很陌生,若不是可以因此不上课,他们怕是连去参加的欲望都没有。
台上老生捋着长长的胡须,闺门旦舞着长长的水袖,小丑晃着光光的脑壳。再加上艳丽的戏服,精致的妆容,高亢的唱腔,孩子们倒也乐得热闹,看得津津有味。
而对于七十年代出生的我来说,看戏时平添一份融入骨子里的亲切,因为这一切曾是我童年中最快乐的一部分,直至今日仍会在怀想中扬起嘴角。

儿时的文化生活十分贫瘠,没有《中国好声音》,没有《梨园春》,没有《欢乐喜剧人》,手机这个词还没诞生,唯一的公共娱乐设施就是广播。那时候呆呆地站在电线杆下听广播足以使我满足。
后来哥哥弄了个破收音机,我们兄妹几个挤在一起听评书《岳飞传》便成了人生盛宴。尽管把天线这样调那样拉声音还是嗞嗞拉拉,但是刘兰芳的声音依然有滋有味把我们迷得五迷三道。
苍白的童年需要色彩,逢年过节,赶会便成了我们生活中最浓艳的一笔。
那时一起会,方圆多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高高的戏台,各种卖东西的,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母亲会给我两毛钱让我去赶会,我常常捏着两张一毛的角票如同握着一笔巨款,郑重地在一个个小摊前斟酌:一串米花团子五分钱,一棵甜蔗秆五分钱,一碗凉粉一毛钱,一把炸红薯片两分钱,转一回转盘两分钱……反复盘算之后我常常选择转转盘,因为两分钱有可能转到米花团子红薯片甚至泡泡糖。
不过我很快就会牢牢装好剩下的钱去看戏,因为看戏不花钱。
我一般不在台前看,而是到幕后。那时的后台是用高高的高粱秆围起来,我便扒开一条缝,小小的脑袋夹在缝里看人家化妆。尤其喜欢看旦角:粉白的底色,夸张的腮红,入鬓的柳眉,黑黑的眼影,艳红的樱唇,高高的发髻,在我眼里美到了极致。还有那翘起的兰花指捏着细细的笔时而描眉,时而点唇,时而打腮红,时而勾眼线,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常常令我痴迷。
那个时候我总觉得戏里的相公们为娘子神魂颠倒实在是应该的,真真是好看得紧。
看旦角化装停当,我便和人家一起等,人家等着上台,我等着人家上台了再往台前撵着看。在等的时候我便极其崇拜地听人家聊天。那时总觉得天仙一般的人儿说出的话定然与俗人不同,所以当从那好看的朱唇里吐出的依然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家乡话时,我总会有种莫名的失落:怎么是这样,我一定听错了。
儿时的我又哪里懂得,戏外的普通人演着戏里的感天动地意切情真,吸引着看戏人或悲或喜,谁是剧外人谁是戏中人恐怕真的说不清呀。

但我很快便忘记了旦角带给我的失落,依然如铁粉一般追到台前,看她轻移莲步,红裙微动,垂在身后的长长的发掠过衣袂,回眸间千娇百媚,明艳动人。我痴痴地盯着,直到她长袖一挥,两袖交迭,斜斜举起,如惊鸿一般翩然而至后台。
这一幕便刻在我的记忆里,再也拂不去。
于是我和小伙伴也学着唱戏,砰砰跳的心悸动了童年的梦。
我们趁大人不在家,关上门,扯下床单披在身上,拿起枕巾用皮筋扎在手腕上,把面粉涂在鼻梁上显得高挺,双唇舔湿咬着红纸便有了红嘴唇。然后几个傻丫头甩着床单,舞着枕巾,举着胖乎乎的兰花指,移着小碎步,模仿着舞台上的丫鬟小姐相公家丁,真是你方舞罢我登场。被单枕巾在狭小的屋子里挥来舞去,我们难免被拖在地上的被单绊倒,于是大家便你压在我身上,我躺在你腿上笑作一团。
若这时大人回家的脚步声传来,屋里更是手忙脚乱。铺被单的踩着放枕巾的,放枕巾的碰着拿面粉的,床单铺反了,枕巾放歪了,面粉弄洒了,脸上的忘擦了。待家长进门,几个小孩若无其事地写着作业,红红白白的脸早已坦白了一切。
当然大人的嗔怪无法掩去这种偷偷摸摸模仿所带来的兴奋与刺激,我们常常乐此不疲。直到比我们更小的孩子也开始偷着唱戏,我们才猛然明白:自己已经长大了。
于是卸下床单枕巾,洗去白面红唇,把所有的浓墨重彩和流转的裙裾一同尘封在记忆里。在无数个以后的日子里,偶尔想起这儿时唯一的彩色照片,仍会神往地微笑,满足而庆幸!庆幸曾有这样一段时光照亮了我的生活!
戏说童年,童年如戏。岁月的打磨使这一折戏历久弥新,滋养着我的生命,让我在写下这段文字时依然可以如当年一样兰花指翘起,轻贴在腮边,回眸望向那久远的一页。

作者简介:徐晓,海南省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语文教师。我写,只是因为我喜欢文字带给我的满足和宁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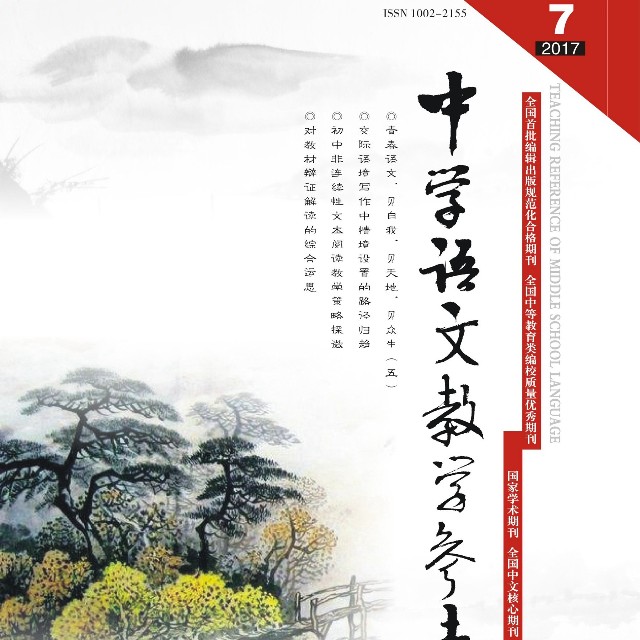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河南站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河南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