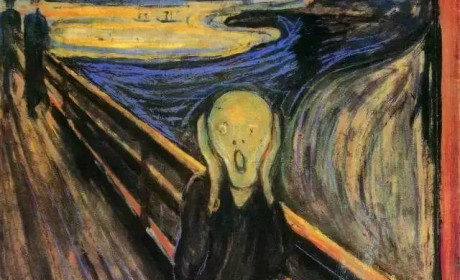加缪:荒诞的世界里,我永远是局外人

1957年的深秋,四十四岁的加缪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
他已年届不惑了,但对于这个奖台而言,他则太过年轻和耀眼。
毫无疑问,他是个文学天才,也是最年轻的诺贝尔获奖作家之一。
26岁就写出了不朽名作《局外人》,29岁发表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的神话》,34岁时长篇小说《鼠疫》再次引起文学界的轰动,44岁那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
岁月已经爬上了这位天才作家的脸,但并未摧残他面容。
他依旧是波伏娃口中的那个“帅哥”,只是时间将他眼神中的忧郁转变成了深邃。
他扫视台下,用清晰有力的法语开始获奖演说:
二十多年荒唐的历史进程中,我同我这代人一样,一样的茫然无助。
在时代的剧烈动荡中,仅靠着一种情感模模糊糊地支撑自己:写作的光荣。
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写作就是承担人类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对人类提出的种种问题”,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加缪的评价。
加缪完成《局外人》时才26岁,很难想象在如此年轻的躯体里,已经住着一个如此沉重的灵魂,已经开始担负这样的使命。

《局外人》
作者:阿尔贝·加缪
豆瓣评分:9.0(44872人评价)
《局外人》的开篇
《局外人》开篇第一句便是: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
主人公默尔索对于母亲的死期显得并不关心,当问及母亲的年龄时,他也搞不清楚。为母亲守灵时,他并未流露出悲伤,一如既往地喝着咖啡抽着烟。
葬礼后的第二天,便和女友一起游泳,看喜剧片。
当女友玛丽问他是否爱她时,他回答,不知道爱不爱,大约是不爱吧。
当女友问,是否愿意和她结婚时,他觉得结不结婚不重要,但为了不让女友失望,他愿意结婚。
当道德可疑的邻居请他帮忙处理一起桃色事件时,默尔索并未拒绝,认为没有理由让他不满意。当邻居说到“你现在是我真正的朋友了”。他觉得做不做朋友都行,于是就接受了这个朋友。
当老板想要提拔他去巴黎发展时,他觉得自己没什么热情,就没接受。
无论亲情、爱情、友情、事业。他都是一副漠不关心,可有可无的态度。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误杀了一个阿拉伯人,被代表公正的法庭“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判决死刑。
加缪在《局外人》英文版序言中写道:
“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着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
如此负面的角色,为何成为《局外人》的主人公?
为何一个看似负面的角色,却受到作者如此的肯定和钟情?
首先,分析一下小说为何取名为《局外人》。
这部小说在其他译本中也被翻译为《异乡人》,说到“异乡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卡夫卡的《城堡》中的主人公“K”。
代表“荒诞”的卡夫卡也正好和加缪写的主题暗合,《城堡》中的“K”便是这样一个“异乡人”,他来到陌生的地方,世界处处充满着敌意,任何周围的人和物即陌生又疏离。
默尔索也是这样一个异乡人,他有着自己的沉默,无法融入社会制定的那套“潜规则”,他是个被疏离的人,像个异乡来客。
在社会不断压迫下,被粗暴的驱赶到自身之外,成了一名“局外人”。“局外人”和自己的情感是疏离的,所以看起来是冷漠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并非真的冷漠,也不是全然麻木。
他爱自己的母亲,每次都像个孩子一样叫她“妈妈”,而非成年人常用的“母亲”。
他总会怀念“妈妈”,点滴的回忆中流露出怀念和依恋。他对生活也饱含激情:
“我曾经在那里发现了我最可怜、最深刻难忘的快乐:夏天的气味、我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玛丽笑容和裙子。”
被审判的主人公——默尔索
审判中,人们绕过了杀人的事实,对默尔索进行道德审判。
将他描述为一个残忍麻木的人,有预谋的杀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参加母亲的葬礼,精神上的弑母者。
一个单纯的冲动杀人案开始变质,犯人被妖魔化,人们搜集种种“证据”来证明默尔索没有人性。
无论是公众、媒体、检察官还是法官,都急于置这个“邪恶”的犯人于死地,好展现他们的正义。
默尔索的悲剧至今还在上演,人们总是乐意展示自己的正义,为此急切地给他人打上邪恶的标签,然后把这些“邪恶”的人置于死地。
“正义”像一剂醉人的鸦片,每个人都急于“正义”,没有人关心事实的真相,于是默尔索成了这场“正义”狂欢的牺牲品。
同样命运的还有不久前,被网络上“正义”网民逼死的安医生。
加缪如此总结《局外人》: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一个在自己母亲的葬礼上都不哭泣的人有被判死刑的风险。”默尔索的罪不在于错杀一个阿拉伯人,而在于他不愿意说谎和表演。
这个社会有一套矫情造作的潜规则,谁不遵守就是社会的公敌,就是揭穿“皇帝的新衣”的傻瓜。
母亲葬礼时,他只需表现得沉默和悲伤便会得到旁人的赞同;女友问爱不爱她时,他只需不加思索地回答道“爱她”,便能讨得女友欢心;
预审时,他只要说谎自己信仰上帝,愿意做基督的羔羊,便能被预审法官谅解;法庭上,只要他愿意说谎,或是装作发自内心的忏悔也能免于一死。
他不会说谎也不会伪装。
当世界都在说谎和伪装时,他不这样做,就成了罪犯。
正如加缪对《局外人》的注解:“这是一个没有英雄主义,为了绝对真实而情愿去死的人的故事。”
《局外人》的价值
《局外人》不简单是一个关注极端刑事案例的故事,更是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
小说中多次出现一个意象——阳光。
去往母亲葬礼的路上被阳光照得昏昏欲睡;
守灵的夜晚,刺眼的灯光照在白色的墙上也是阳光意象的变种;
葬礼上,燥热的太阳让默尔索烦躁不已;
默尔索杀死阿拉伯人,是因为被太阳晒昏了头,烦躁之下,无意识杀了人。
阳光、燥热、弥漫的尘埃,整部作品的前半段的充斥着这样的基调。
阳光这个意象正如社会这个群体对于个体的压迫。
在干燥和灼热之中,在刺眼的阳光下,默尔索被抛到自我之外成了“局外人”。
正如在社会的潜规则下,在群体的规制下,个体的独立性被剥夺,默尔索不被允许做一个追求真实的人。
就像北岛说的:
“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他不懂我的沉默,我们交换的,只是一点轻蔑,如同相逢在镜子中,对于自己,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畏惧黑暗,却用身体挡住了,那唯一的灯,我的影子是我的情人,心是仇敌。”
世界是荒诞的,不合理的,对于不懂规则的人甚至是充满敌意的。
不仅默尔索先生,每个人都会面对着这样的困境。《局外人》是个悲剧,默尔索用他的牺牲揭露了世界的荒诞。
看到荒诞,然后反抗荒诞。
无论是《局外人》中的默尔索,《鼠疫》中的里厄医生,还是《西绪福斯的神话》中的西绪弗斯,这些人物都是加缪眼中的英雄,反抗荒诞的英雄。

(语人读书本期封面,图片来自煤炭工业出版社《局外人》)

 语人读书
语人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