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特·安德森生命之书:遥远的声音,寂静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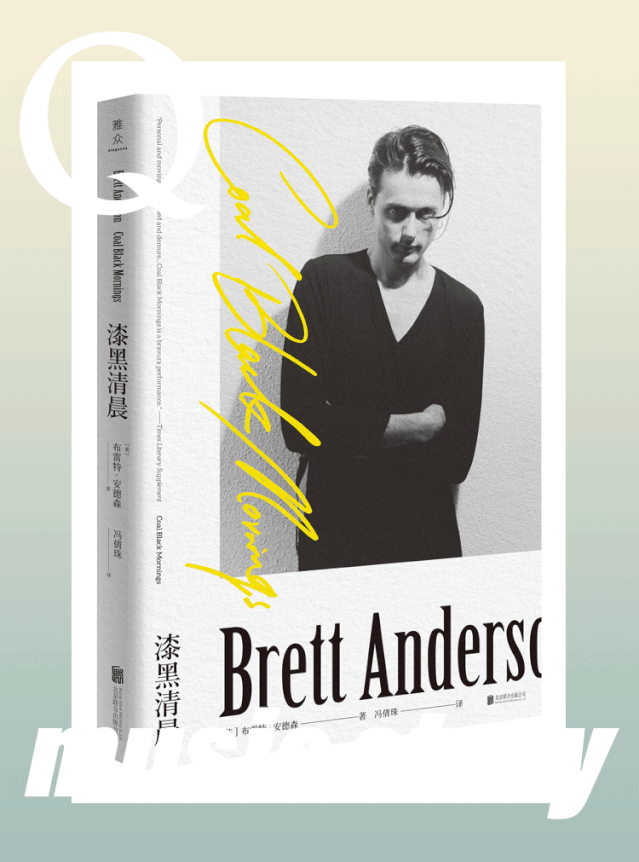
《漆黑清晨》不是一本关于山羊皮乐队(Suede)的书,而是一本关于布雷特·安德森(Brett Anderson)生命的书。字里行间满是典雅、忧郁,以及隐含着不稳定性的自我探索。和这位传奇乐队主唱的舞台形象相比,迷人处有过之而无不及。
2019年6月,笔者参加了巴塞罗那闻名遐迩的春之声音乐节(Primavera Sound Festival)。地中海的干燥、深夜独行、体香、潮水和音墙已成遥远的回音,脑海里却没办法移去这组影像:某场演出间隙,身旁站着一位约50岁,纤瘦,身穿灰色西装,刘海向左,看上去郁郁寡欢的中年男人。他一手抵着嘴唇,一手自然地插进口袋里,眼睛盯着舞台,神情严肃,仿佛在思索某个足以改变他生命的难题。笔者已经忘记那刻台上演出的乐队是谁,只记得意识到总盯着陌生人看没有礼貌,又觉得如果和这个人互动会打扰他思索,便垂下了头。
这场演出结束很久之后,笔者才在某个时间点突然想到:“啊,他很可能是布雷特·安德森。”但无法证实此事是否为真。当时并没有去看山羊皮在春之声的演出,也没有刻意记住那个男人的样貌。见到偶像本来是件好事,但这次模棱两可的经历,让那个疑似布雷特·安德森的人成了一种随机、独立、不附着于这段时期而又难以排解的苦涩滋味。
由冯倩珠翻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在年初出版的布雷特·安德森自传《漆黑清晨(Coal Black Mornings)》,以类似的方法处理了类似的记忆缠绕母题。这个故事自1967年布雷特出生开始,到1991年乐队进入主流舞台为止,完全不涉及山羊皮成名后的历史,无关乎乐队解散和复出的历程,甚至并非布雷特·安德森陈述艺术追求的舞台。事实上,就连日后的乐团成员,都是在书的进度发展到75%时才终于凑齐的。
《漆黑清晨》由一连串苦闷的记忆微光组成,叙事并不指向某个终点,也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安德森在前言自述:“这是一本关于失败的书。”我们的英雄已经老了。这个故事是安德森人在中年,到了能够自我接纳阶段的必要产物。
我们见到的是一段又一段的事件,它们按物理时间发展的顺序排列出来,但实际上具备超时间性。布雷特·安德森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往往会将人物的行为和场景交织得巨细靡遗。但随着思路所至,他又突然在意起当事人某一天的衣着来,或者是考虑到这个“当下”会在“过去”和“未来”起什么作用。
布雷特在行文中大量提及影响自己的音乐,以及他从艺术、建筑、文学......总而言之各种资源中得到的灵感,还有他消化这些资料的方式和这些资料间可能的相互关系。
乍看之下,就像所有博学但话有点多的人那样——他以可以被称为“自溺”的优雅语气娓娓道来,这些资料的详尽实在太过突出,与时间处理上的模棱两可形成鲜明对比,似乎他根本不在乎精确性和相对脉络。布雷特字里行间对无数乐队、艺术家和文学作品如数家珍,或许仅是他以疏离的视角观察包括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时,自然反刍泄出的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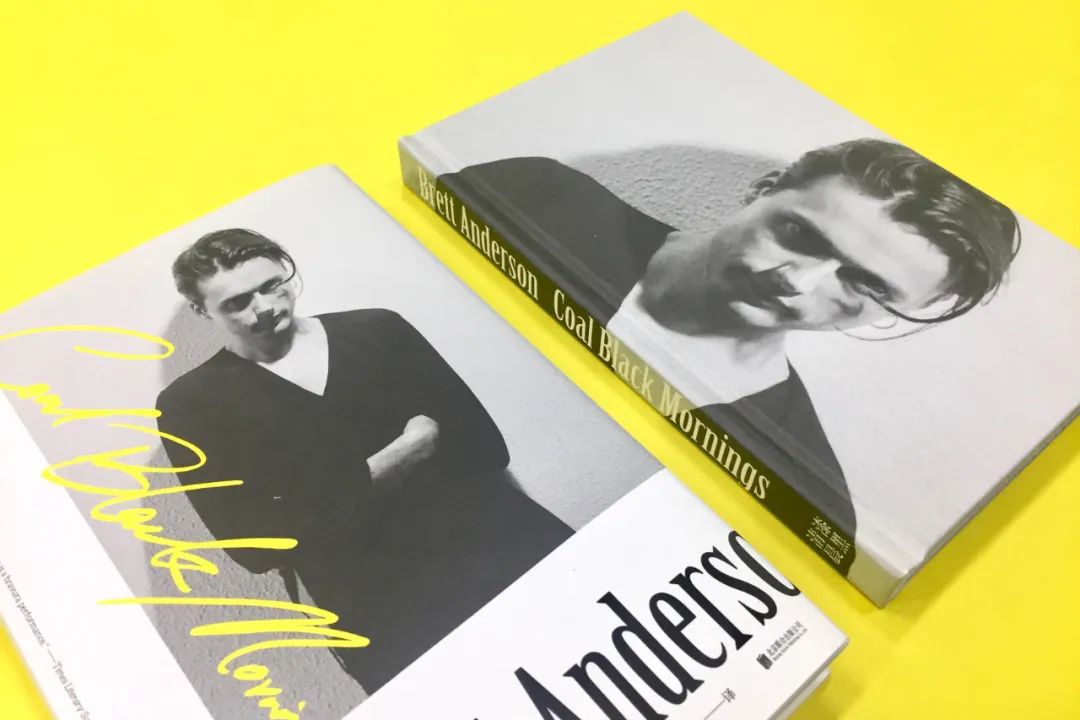
这个故事的核心是布雷特·安德森相对匮乏且平凡的童年:“我们家所有东西不是自制就是二手的。”布雷特的父亲性格刚愎、不容置疑,因为多年的底层劳动,养成了各类让人不悦的表达习惯,甚至还有男性沙文主义之嫌,但同时是个慷慨激昂的瓦格纳迷。
父亲也有温情的一面,他会在下雨的清晨当小安德森骑着脚踏车去送报时,手持外套,一路追赶上去。布雷特的母亲则是这样的:冷静、沉默,有艺术天分,却因现实所迫,以为富人家缝制品位不凡的衣物、修饰家里的彩绘壁纸、安排灯光配置、添上绘画作品为乐。
她会在孩子身边阅读近当代作品和古典诗词,并以强制手段要他们珍惜得来不易的食物。比起父亲对英国海军上将和德国作曲家那种具排他性的忠诚,家里这对被母亲影响的小姐弟更多地拥有了一种广泛的对于思索和艺术的爱。
日后更早离开家里的姐姐坚毅果敢,正是她带着小安德森认识了摇滚乐。这些飘动的火苗会在这本书结束以后的时间里燃起,但在小安德森的童年时期,这都被困在了那幢干瘪、阴暗、其貌不扬的小房子里,而这处小镇也不过是伦敦和布莱顿(Brighton)之间某处不起眼的无名城镇。
直至到曼彻斯特求学之前,布雷特·安德森都在这所小房子里和亲人生活。他倾注曲折的思索和优柔寡断的爱来处理这段记忆。父亲因为遭受过爷爷的暴力,立誓绝不对孩子动手,但生活中的压力逐渐转换为难以隐藏的尖锐表达方式。即使在山羊皮成功后,父亲也会难以抑制地批评他们的音乐。
安德森在这一段叙事中加入了宿命论的悲观色调,像艺术家使用凿刀重复涂抹、刮去......因为他始终没有弄清楚如何理解父亲,也完全无法不去在意父亲对自己音乐的评价。对于母亲和姐姐的判断就容易得多了,她们敏感、神秘又有威严,是布雷特进入艺术神殿的引路人。但事实证明,他并没办法跨越眼前所见去洞悉母亲内心真正的想法,也就来不及为日后的遗憾做出补救。
在这些或近或远,或明晰或朦胧的关系到核心家庭成员或亲戚熟人的记忆里,有相当比例被写进了布雷特·安德森的词曲作品中。他穿针引线地将来自父母的灵感、某位舅舅的过世或是某位阿姨的意外凑在一起,却有意无意地省略某些细节让这些元素之间关联性降低。
如他自述,在遇到日后的乐队吉他手伯纳德(Bernard Butler,1994年离队)之初,他还没有很好的音乐感觉,而是叙事和抽象的想法先行。在那些同时在反思和积累的日子里,他像是个调度自己记忆的导演,在剪辑遇到困境时,就补拍一些镜头,让演员唱歌,让歌声联结那因主观的时空错乱而疏离的记忆。但在书写此书的“未来”时,他则再次陷入过度阐述自己当初“想做什么,因为什么想这样做”的循环里。
现实生活中的歌手还在期盼寂静的生活,但这个故事结束于即将到来的清晨。1991年,布雷特和伯纳德还在为作曲苦恼时,过去20多年的尝试和困顿终于水到渠成:“他把我领进公寓,激动地给我听一支曲子的小样......我坐在公寓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在打字机上敲打。我心里明白,乐队要走上一条不一样的路了......这些歌不再是软绵绵、不成调的空洞产物。我感觉我们终于找到了力量,我们挥舞手脚反抗时代的庸常,这反抗带着一种风格、一副灵魂。这种音乐最终定义了一个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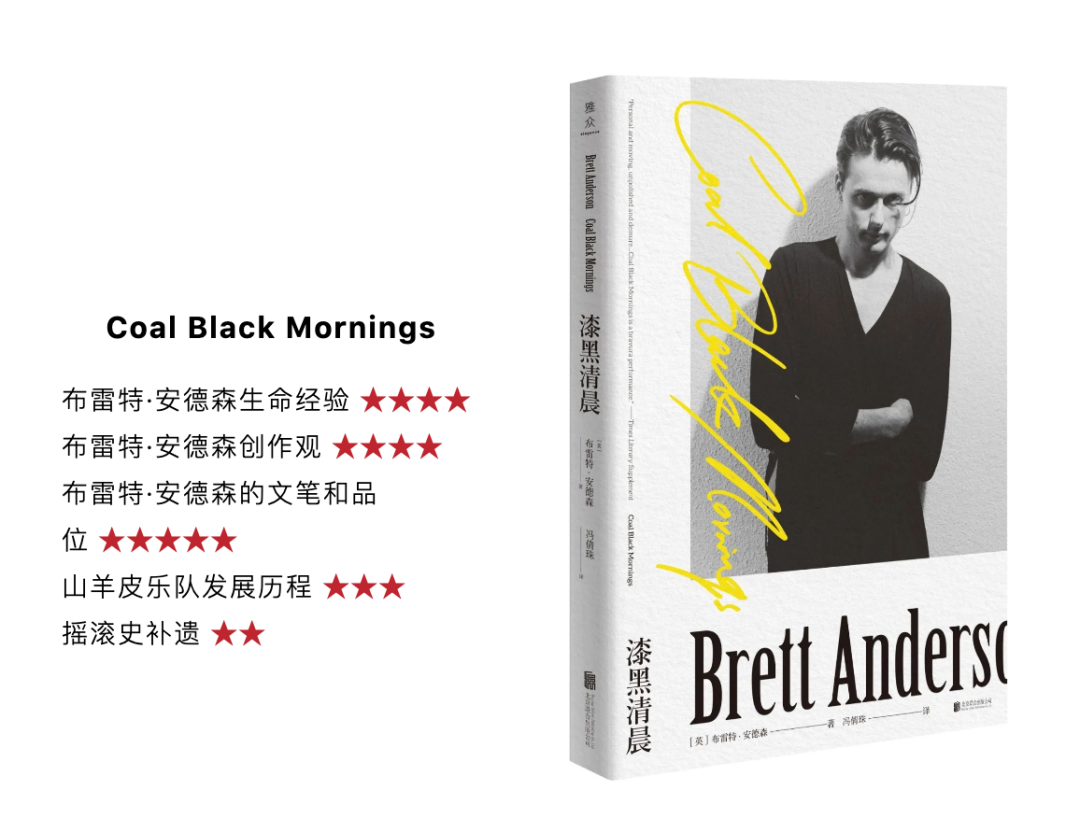

 Qthemusic
Qthemu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