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秋梅:那走街串巷的吆喝
清晨,我沿着小区附近的路慢走,想找到那个卖苹果的老大爷。
他的苹果可真甜,价格又比超市里便宜得多。可是连续三天都没有找到他,我想他不会再来了,有些失望!
忽然,那个戴着黑色有沿帽、穿着黑色夹克衫的老大爷出现在路边了。我惊喜地跑过去,边往袋子里装苹果,边和大爷闲聊。才知道,上一次他卖苹果,被城管把电子秤收走了。求爷爷告奶奶的好话说了一箩筐,甚至下跪了,也没有要回他的秤。

我要的苹果多,他的神情张皇不定,一直东张西望,害怕城管再来。称好了,差5分钱不够一个整数,他却又送给我一个苹果。
我不敢评判城管的对错,忽然怀念起那走街串巷的吆喝。
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的每一个清晨,卖豆腐的良叔,总会在人家大门口吆喝:“卖豆腐唻换豆腐,又白又嫩的豆腐来喽!”我们家很少有现钱,多半是盛上一碗黄豆去换豆腐。弟弟捧着一碗黄豆,我端着一个盘子出来了。良叔看见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用小刀划上两小块豆腐,一人一块放进我们嘴里。然后接过碗,把黄豆倒进一个小筐里称,口算出多少豆腐。我高举着盘子,他轻轻地,还得俯身才能放好豆腐。
豆腐拿到家,用小葱拌了,是“一清二白”的好菜,庄稼人的最爱。我却觉得不如那一小块原味的豆腐好吃,我对豆腐的喜爱就是从良叔的赠与开始的。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吃到那么美味的豆腐了。
春暖花开,赊小鸡的汉子就来了。“赊小鸡唻,不是草鸡不要钱!”草鸡,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母鸡。大家喜欢母鸡,是因为鸡蛋可以换成钱,贴补家用。于是,大妈大嫂、奶奶们就端着筐擓着篮出来了。白色的、黄色的、黑色的、芦花色的小鸡们,毛茸茸地推着挤着,“叽叽叽叽”,呼唤着它们的主人。这买小鸡,可没有人付现钱,因为大家得等着小鸡长大。如果有公鸡就算白送,只付母鸡的钱。
很快,村庄里就跑满各种颜色的小鸡了。主妇们很聪明,给自己家的鸡染上与别家的鸡不同的颜色。你染红色,我就染绿色。你染粉色,我就染一道粉一道蓝。颜料就那么几种,主妇们想尽办法让自己家的小鸡有特色。你染左腿,我染右腿。你染翅膀上边,我染翅膀下边。
小鸡长大了,大到公鸡会打鸣叫你起床了,赊小鸡的可就来收钱啦。谁家几只鸡,都在本本上记着呢。大妈大嫂、奶奶们手心里握着手绢出来啦。钱,都在手绢里一层一层裹着呢,严严实实。照旧的,先不取钱,开始数落赊小鸡的:“我家的鸡死了一只,是不是带出来的毛病?”“你说没有公鸡,我家买了二十只,就有五只公鸡呢!”赊小鸡的汉子嬉皮笑脸:“好好的小鸡让你喂死了,是不是喂多啦?”“公鸡好,公鸡不给你要钱,还能给你们家那口子当下酒菜。”

嘻嘻哈哈中,赊小鸡的汉子收完钱奔赴下一个村子,主妇们也都心满意足地回家了。我和弟弟倒希望我们家能多几只公鸡,天天盼着那些鸡都长出大大的红冠子,养大了,就可以多饱几次口福。
“磨剪子唻戗菜刀,戗菜刀唻磨剪子……”那是一个老爷爷背着一块磨刀石来了。走到村头大柳树下,他就背靠树干坐下,拿出他的旱烟袋。自制的旱烟味有浓郁的香气,烟圈落在他的眉毛上,飞到他的白发上,他就像一个慈眉善目的仙翁。小孩子们是看啥都稀奇的,早就围拢来一圈。老爷爷开始支使离家近的小孩回家端水,被支使的小孩像得了最大恩赐,屁颠屁颠地跑回家。
老爷爷口才好,脑子里故事多。我们喜欢听他讲杨家将,讲诸葛亮。我们越听越不舍得让他走,就回家找剪子找菜刀,甚至找镰刀、铲刀。一会儿,他的面前就堆起一堆铁货。老爷爷嘴里不闲着,手上的功夫更精湛。这些家什在他的上推下滑中,变得光亮起来。老爷爷磨完剪子,还要剪剪布,展示自己的手艺。
“大孩,刀磨好了吗?该切菜了。”“二妮,回家吃饭啦!”“三羔子,回家来给老爷爷拿点吃的。”大人们的呼唤响起,我们也都陆续回家了。老爷爷吃着几家送来的饭菜还有粥,身边还散落着几把铲子。
那个年代,没有城管。大街小巷,不同时段,总会响起各种吆喝。卖豆芽的、卖西瓜的、下乡理发的……只要熟悉的吆喝声响起,村子里就有节日般的热闹。
现在,再也听不到那些美妙的吆喝声了。琳琅满目的大超市,加快了人们购物的速度,却少了那些温情。街上林立的店铺,提升了人们的享受档次,却隔开了人与人的距离。
那些走街串巷的吆喝,只能成为怀念。

作者简介:马秋梅,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冉堌镇中学语文教师,教研组长,菏泽市定陶区初中语文兼职教研员。爱读书,勤写作。热爱生活,喜欢记录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创校刊《冉星》并任主编。文章散见于《菏泽日报》《神州》等报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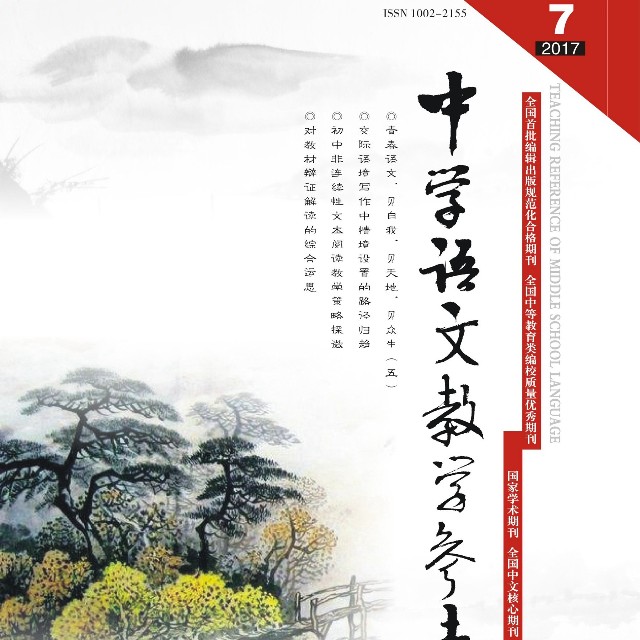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河南站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河南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