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日光流年》:光照不到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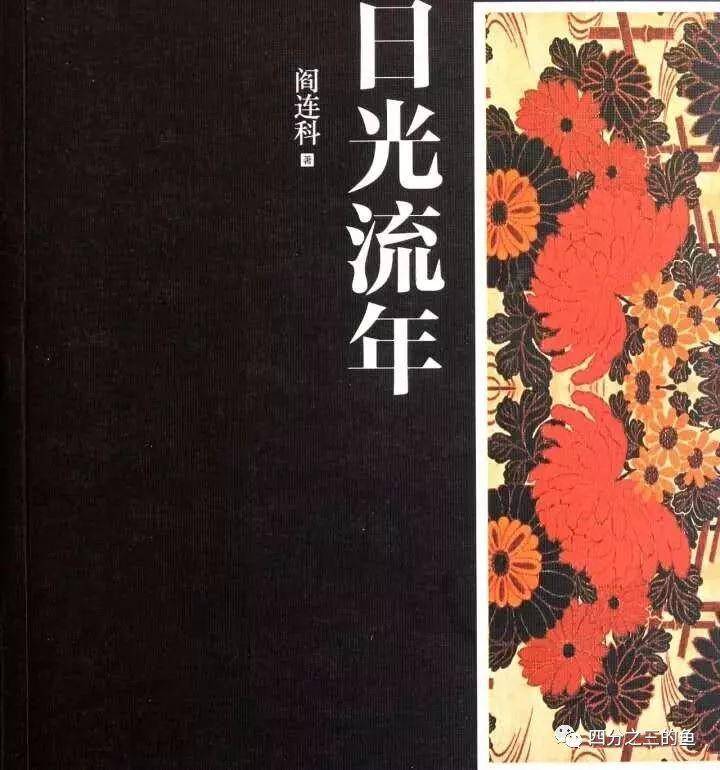
莱昂纳德·科恩说:“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可这世间偏有一个地方,即使支离破碎到不堪,光还是不肯进来,那里只有无尽黑暗。这个光照不到的地方,就是三姓村,出自阎连科的小说《日光流年》。
耙耧山,三姓村——司马、蓝、杜三姓聚居,几代人因“堵喉症”困扰,都活不过四十岁。死就像日出日落,刮风下雨一样寻常又普遍,这导致三姓村像疫区一样和人世隔绝着。《日光流年》讲述的正是三姓村几代人为了长命,怎样苟延残喘地活,怎样不顾一切地改变短命的命运,最后还是被命运抛弃了。
四代村长,为了破除“活不过四十岁”这个魔咒,不择手段,男人卖皮,女人卖身,最后一腔孤勇都败给现实。故事的惨烈程度,像数九寒天中奔腾的瀑布,哗啦啦都是冰碴坠落粉身碎骨的声音。
对三姓村而言,“光”不是太阳,是宿命;“黑暗”,是对命运的绝望。窒息、压抑、残酷、绝望,这是看完《日光流年》的第一感受。
有人问阎连科,《日光流年》的情绪出口在哪里。他说:“文学不承担提出任何问题与解决任何问题的能力。小说写好了,有读者看,有读者记住,就是好小说。”
为破魔咒,各显神通
在小说里,对于怎样破除“堵喉症”的魔咒,三姓村的四代村长各有坚持。
第一代村长,擅长接生的杜桑,他对付堵喉症的方法是多生孩子,死的让他死,出生率大于死亡率,三姓村的人就不会绝。也许每个孩子各有各的降生方式,但成年后等着他们的,只有堵喉症这一条归宿。
第二代村长司马笑笑,热衷于种油菜。只因某天村里路过一个讨水喝的白胡子老头儿,司马村长向他打听长寿秘诀,老头儿说喜欢吃油菜。司马笑笑以为自己找到了长寿秘方,号召全村种油菜。蝗灾肆虐时,他宁愿放弃抢救庄稼,也要全村人护住地里的油菜,只因吃油菜可以长命。最后,粮食短缺,饿殍遍野。还没等“堵喉症”找来,多少村民已先饿死。不言而喻,吃油菜当然治不了堵喉症。
第三代村长蓝百岁,坚持换土,只要把村里的庄稼地都翻一遍,吃上新粮,堵喉症就会根治。为了翻土,劳民伤财殒命,还搭上了自己女儿蓝四十的清白。结果,该发病的还是发病,没人能活过四十岁。
到了第四代村长司马蓝,他要开山挖渠,引进山外的水。为此,又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征人征粮征钱。司马蓝下定决心挖渠时,“堵喉症”已经找上了三十九岁的他。为了延长生命,他需要进城做手术。他需要钱。他用软刀子逼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蓝四十去做皮肉生意换取医药费。最后,七条命,换来灵隐渠通渠,可等来的依旧是死亡的号角。
杜桑死了,死于堵喉症。他一边忙着在全村催生,一边研究《黄帝内经》配秘方,每天喝三碗秘制“苦水”,也没办法摆脱堵喉症。
司马笑笑死了,被乌鸦生生啄死的。被堵喉症折磨的最后时日,大饥荒还在延续。为了让全村人熬过青黄不接的时段,司马笑笑躺在西梁沟,用自己的肉身吸引乌鸦。铺天盖地的黑老鸹,成了村民的救命食粮。
蓝百岁死了,上吊死的,翻土也改变不了村民的短命。
司马蓝死了,他到城里做了手术,完全可以活过四十岁,就在四十岁生日那天,大家发现他死了。司马蓝死于自己的诅咒,“我要不娶你,让别人都活过四十岁,让我四十岁的前一天突然死去,行不行?”这咒是向蓝四十发的,司马蓝终是没有娶蓝四十。
情与爱,尽悲凉
蓝四十是第三代村长蓝百岁的第六个女儿,灵秀动人,她和司马蓝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本以为能顺利地和自己心爱的男人结婚生子厮守,哪想却为司马蓝做了一生的垫脚石。
十四岁那年,身为村长的父亲,为了讨好公社卢主任,让他拉着劳动队伍帮村里翻地,她被作为贿赂品送了出去。蓝四十去献身,司马蓝并未阻拦,只是信誓旦旦地对她说:“无论你侍奉啥儿人我都要娶了你,我要不娶你做我媳妇我天打五雷轰。我要不娶你,让别人都活过四十岁,让我四十岁的前一天突然死去,行不行?”
当蓝百岁自杀,司马蓝再次用“我娶你”为筹码,让蓝四十假传遗言说他是村长接班人。
司马蓝顺利当上了村长,可惜位子还没坐热,表妹杜竹翠无视“村规”想外嫁。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为了守住自己村长的头衔,司马蓝娶了杜竹翠。十九年后,为了凑足手术费,司马蓝跪地请求蓝四十为他去卖身。四十提出的条件是“你离婚,然后娶我”。
只是啊,在光照不进来的三姓村,命运怎肯轻易放过这对有情人。蓝四十死了,死得那样平静,就像这一生都没曾和司马蓝有过恩怨一样。司马蓝躺在她腐烂的身体旁也死了。他们死于对各自命运的绝望,死于不能面对彼此,死了,就也彻彻底底地解脱了。
他们死的时候,都以为灵隐渠通了,有了灵隐水,全村人都能活过四十岁,活到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假若他们没死,闻到了灵隐渠的水臭,又该是怎样的一场疯狂呢?
为了活过四十岁,三姓村的四代村长,像嗜血的魔,他们用暴力夺来权力,又用权力发动暴力,所有的惨无人道,出发点竟然那么简单——活过四十岁。为了生存,或许说得直白点,为了活着,只是为了活着这个单纯的目的,一切道德化为乌有。孰高尚孰卑劣,孰善孰恶,你忍心轻易下结论吗?
司马蓝为了七岁时就萌发的村长梦,利用了蓝四十一次又一次,他爱蓝四十吗?爱。但他更爱自己,更爱至高无上的村长权力,那是他呼风唤雨的筹码。而他呼风唤雨意欲何为?无非就是开山修渠通水,让村里的人活过四十岁。你能说他自私吗?
蓝四十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豁出去,只是为了一次又一次成全司马蓝。她一生活在三姓村的蜚短流长中,像黏在别人衣襟擦不掉的浆糊,却永远是司马蓝心中的白月光。
日光且长,流年短促
《日光流年》写得夸张吗?是魔幻,是荒谬?如果你愿意发现这个世界的荒谬,就不会觉得它夸张。亦如阎连科自己所说,现实远比小说精彩,关键是你是否有能力把它写出来。
《日光流年》的文字是一大特色,蓝汪汪的羊叫、白惨惨的惊恐、冻得哆嗦的空气、风风雨雨的说话声,这些不拘一格的修辞运用,让文字的视觉冲击力倍增,及大程度地增强了阅读体验。而“时光倒流”的叙事写法,又让故事耳目一新。阎连科从主人公司马蓝的死开始写,倒退着一直写到他的出生。寻找来路,方知归途。回看他一生的作为,无非是拼尽全力去实现改写命运这个理想。
阎连科的文字冷峻,他用全知视角,冷冷地刻画三姓村的荒谬,让人不寒而栗的同时,却又能触摸到几许暗藏着的柔情,在那些生死纠缠的残酷中,时而蹦出“午时的炊烟舒缓袅袅地升上来,人间的气息馨香凛冽地扑进鼻子”这样柔软的文字,在压抑下,轻缓一口气,像在恒久的阴霾中见到一丝脆弱的光。
如果翻开书的刹那,你觉得故事压抑、窒息、绝望,没关系,直到看至最后一页,这种感觉也不会消失。不知这复杂的情绪里,可有包含作者内心的孤独,和他无法言说的对这个世界的某种绝望呢?
那么,《日光流年》里到底有没有光呢?
阎连科说:“我觉得写作最难的,不是把黑暗写出来,而是在黑暗中写出一点点善,一点点光,一点点对神的敬畏。”《日光流年》里的光,就是每个读到这本书的人,在心底泛起的怜悯、善念与敬畏。

 四分之三的鱼
四分之三的鱼




